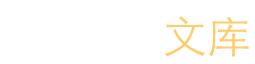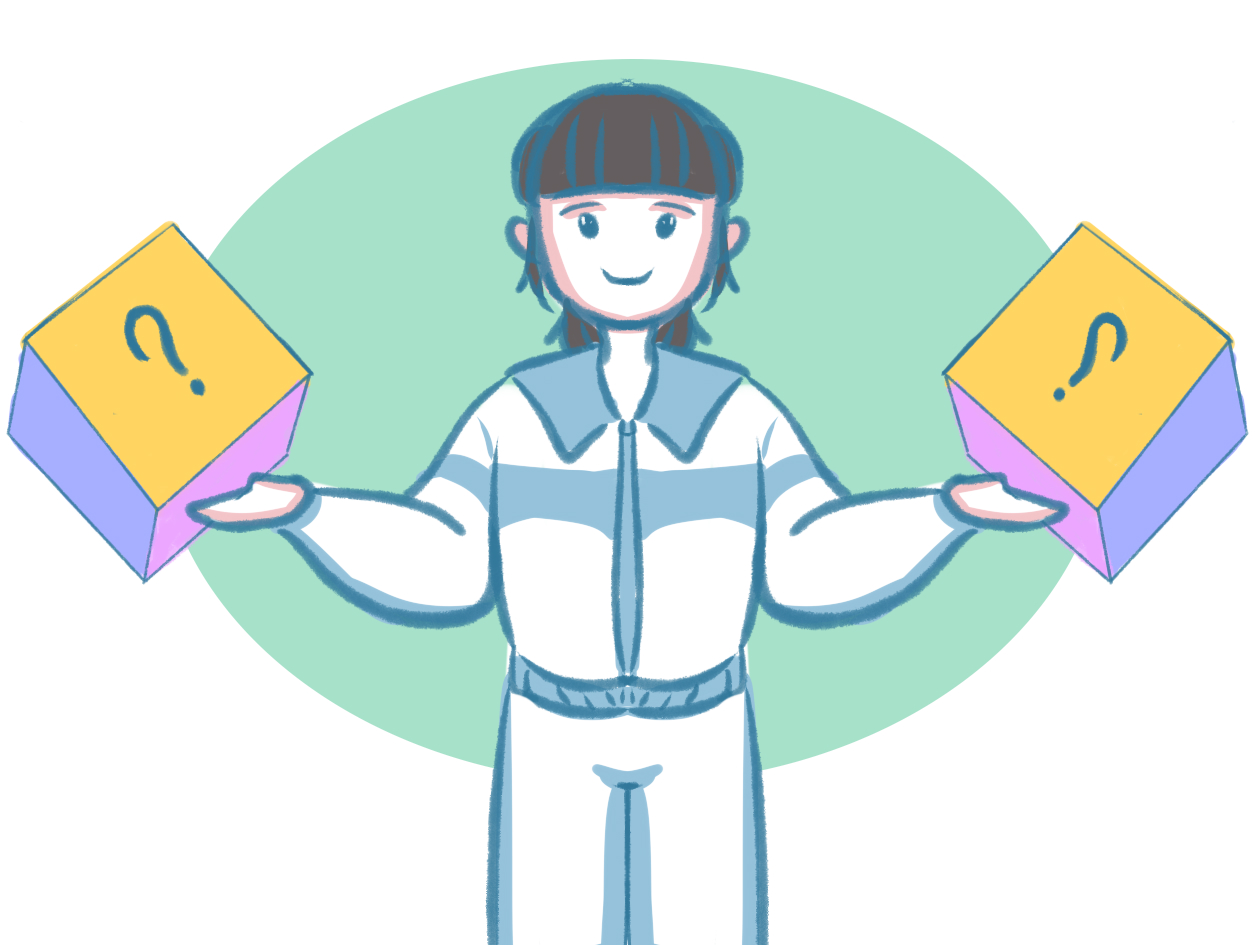旭日偏东,近八时,已经升起在东隅,紫蓝或褐乌色的树林,座座飞檐挑脊的廊桥,在她的光辉下,是旧时古城的往昔岁月和仿苏仿浙的斗拱风情。
骑着自行车,睹此一切而暗叹:应该有一个好心情,没有雾霾,亦无寒风,没有大是大非大事情在前面的办公室内,一切如此平静,只有行驶的车辆,却又悄无声息的来来往往,只有东天的旭日光辉,亮堂堂普照着冬季的早晨,并不喧哗,轻轻微笑一般。
这样的早晨好像是在刚才,又宛若非常遥远,不认识却明白的经过,也许是在梦里,或者只在梦中,才对得起这种或那般的宁静、明亮和浓淡相宜的色彩。也只有“咣”的一声,一天又要过去的傍晚,暮色垂下的下班时光,方可以书写这神秘的光阴,慰藉灵魂,与中年岁月相映相伴而默契的美好时光。
是啊,一天的时间,在打写千字多的文字之后,再去一趟《学校发展报告》的公差,贴一张关乎谁谁职称的《公示》,诸如此类的杂役之际,天色“咣”的一声,从东方一下子落在我的窗外,窗外的西面,等待了好久的暮色“呼”的一声过来,是至高无上的一双黑色眼睛的光泽,普照了我的整个世界,无论是心灵还是我中年的身体。
应该有下弦月的夜晚,在不远处,正悄无声息却又巨大无比的暮色之外,渐渐展开在这同一神秘的世界之间。
翌日,夕辉映射在东面的杨林之际,萧瑟而只剩几片枯叶的枝桠,如简洁、最为真实的生命蓝图,或者说是生命得以畅通与活动的经脉血道。
每当见此冬季的杨林,便浸染庄严、周正的触动,不必悲观,那端坚定。坚定惕剔,是壮怀激烈的美的感受、美的愉悦。所谓“西风残照、谁家宫阙”;“一弯残月,黎明西流”;“暮色苍茫,孑然归宅。”
是的,四十多岁的人,已经听到光阴落下的巨响,不再所谓梦幻编织,魔怔癔症,试看未来,还有二十岁、莫非三十岁光景,却已然如月西流,如暮速降,快哉逝哉,一切的言行便以此有限的生命为限的---站在生的本土和死的界碑一侧,说一些话,做一些事,遵循死的生的标准,来判断、去选择,正如是是非非者,必有论断,已是证明。
那生的意义,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下班归途,见此萧瑟杨林,林后那蔚蓝蔚蓝的天空,无缕缕丝片的云,那蔚蓝的天宇将遁入黑夜,在下半夜的西面,映照出那峨眉山月。夜与蓝天毗邻,相接是辉煌的暮色返照;生活中的鉴人别事,顺势顺时顺天条地理,而远之敬之,或者反动之,好恶在人胸腹,美丑了然于观。
常常工作之时,可想到那些革命者,在给予和努力、甚至奉献中,享用价值观遵循的欣悦,看那笑颜花开而享用的自足,看天下同志者,走在寂静的夜路或明亮的热烈的光中,人性相通以自尊共荣,缘故已知生,便知死;已见朝晖,便知暮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