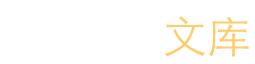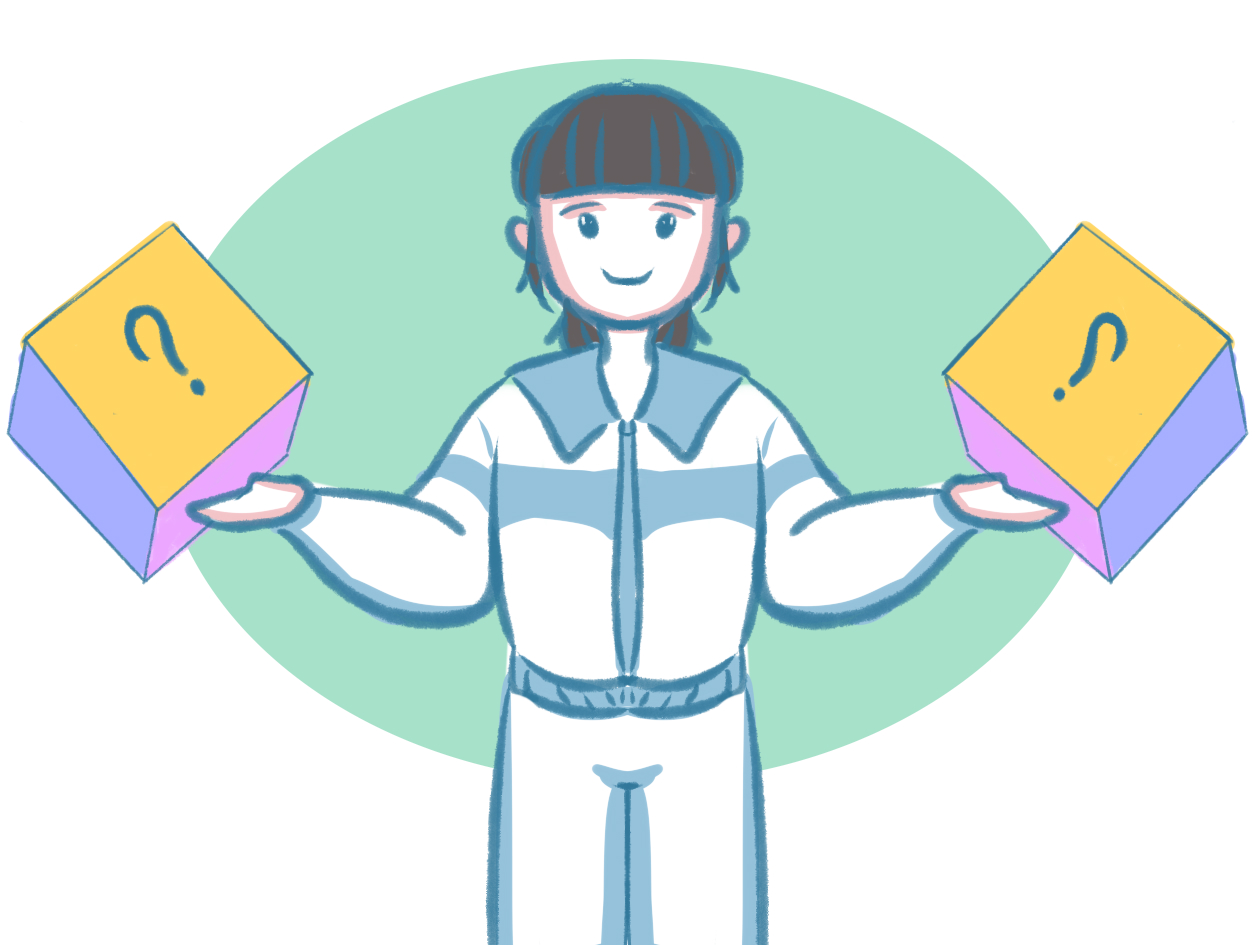天空渐渐由昏暗变得光亮起来,屋檐下残留的瓦片黑亮的影子映着蓝蓝的天下,画下一段连续的虚线,最终砸起细碎的水珠而消失。
欢快一时的鸭子、鸡仔经不住气温的下降,除了小崽崽们还指望,大老爷们原地不动,最多防不住的展了展半步翅膀,又闭起了双眼昏昏睡去。
想来下雨天也无事情可做,盘算着下透雨过后农村的事情又多了。起来捎带孩子的身影,怕把好衣服裹上脏泥浆,嘴里叨叨絮絮叨叨不停。有出门做点什么的,开门看见远山坡顶上正飞升的朵朵残云,蓝莹莹的天空和有点挂不住眼的干净,不自禁张开喉咙并做了个愉快的懒腰。
想要带伞总不用打开,一着悠闲的出去走走,外面有残留的雨露,外面有春天水路的稀泥。或者说臭说香,体味久旱的体会,久旱的心思。
窗口只能输进着大地的采乐部分,不知那太广阔的弧形也是否一样异地的总有相会的时候,来说明只是这残酷的气息有很多的混乱的事情,那杂草丛生中传来的水流哗哗声,听起来比以前更加的壮观。早早的把全部包盖住,陆地上的琐屑小事情,天地进入另一种和谐,也许对我来说却更加的繁琐了,雨天将来的更长。
风把阳光送到了山野的林间,一条龙的姿态,横冲直撞,紧密的树干之间咆哮着,深深自豪的满足欢欣,一片激发豪情的意境。
离别速成的喧闹环境,换了一个产生不同共鸣音的空间,想要以随心,而油然即起的壮志,不敢说吞吐挥发的功力,追求新鲜的格调,以求和谐。
山石堆砌起来,土深陷下去,在那曾经一毛不拔的黄冈土地上,已经长出了盖世文明的臭草,听说只能火攻才能消灭,但现在早已经是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或者路人无故地践踏熟悉成效罢了。
山中的枯草在庄稼收完以后,也在久无干预之中沉静下去,不时出现几棵落叶,栎栎松树得那么苍翠皮,带风吹来草洞一片。看远远的稀疏的树木,有那么一种掀翻天地的感觉,太干了。
火都烧得起来了。
风的力量渲染着人心的抖动,平静寂寞了许多日子的心才恢复过来,努力升华出这种感觉,希望发扬光大,把身形随波极地带飞起来。轻飘飘的饥渴,接触到较劲的热浪,烟,被欲望消失的疲倦,浓浓的又压上了心疼,夹杂着睡眼惺忪之中疏散了几片对活动的对抗。他在爆裂的光照下膨胀起来,风无法,人也无可奈何。
赶快挪动到林荫树下吧,在枯枝败叶之中枕着手,用树枝扫动着热气。山上的风过着重云的氧气,向春朝朝洞的蚂蚁连带班卷着几块百花花的棉花,云山上的天空在氧气里互相运存。
氧气是蓝的,染蓝了天空。
也好像是充斥着天空存着反了新的棉花枝,蓝得更清,可曾想到以后的蓝天,不过也如此飞升度化的雄心凌空,踏遍天上云朵的足影,昭然飘舞。要飞快的变化,能超脱土地的烘托,大海的水浮上来及空气摩擦,天地无形我心五官弥漫,或者根本不同的弥漫每一集,手头之间只是一个有明朗而化作的虚无。
或许真是一种意境的飞腾,这一高度,若我雄心岂是俗夫的幻想,尽管能落后的实地回想,感叹好笑也罢,连自己也退到了远远的地位上了。
感谢上帝,也谢谢三级天空的赋予人,无论走到哪里便能与共设的环境走一起,天籁之音只是有意者爱之,无意者攘之。
春雨久久下不来,阳光却没有减缓丝毫,大地被蒸干的有些枯萎,也很是长时间没有浓妆了,但气候草就过去,老是把风当伴,简直枯燥的乏味之际。
空气干燥,人的火气就容易生出来,受气的身心影响,老有那么一股焦黄的感觉,包都包不住,不时想睁大双眼看世界,可是脸眯着眼睛一条缝的去看。也不敢有我偷偷的亲了山还要亲切,山势模型太渺小,送来热干之风连眼也不清晰的看我。恶心的苍蝇叫嚷着,翻着我的胃,从早到晚打开窗户连风吹微尘,进来也不怕事,甚至以恭敬的送出,但其任不厌烦地在小屋中飞来飞去,连带了不间断的嗡嗡之声,着实让我愤慨却也无奈。
和小虫子斗心,还不如弄一点药,整死了了事。苍蝇真是个无聊的祸害,无论怎样从科学的角度来评定,他就是给不起人一个答复,老是自以为然的行为,只是烦透自己。
能走进昏迷,也能从昏迷中走出来,身在一个世界奔忙,耳朵听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一场行走一场幸福,好比到了一阴阳地界之后回过头来头昏脑胀的现实。
人是吃五谷杂粮的,也还是要睡噩梦床的,好像整个世界的外形不是言而闫润的气势菱角分明,那锋利的一面随时随地指正着,醒来之时还是醒到了惊恐的影子。其实现实并没有到这一步,也不厌困境,生活的回城之中遇到问题,那么就解决问题,必能承受问题的最劣等的后果,也就去恢复正常的心上的生活,只是魂牵梦断于这个世界,想要逃避开,想要对抗,想要回还必扰其中反击的时机。可惜梦中的人有仿佛连自己都有些不像,能想,却没有轨迹能为,且无形之中绑住了手脚或可原地踏步,身不由己,回想起来也不知道是当时被肢解了还是一条。或者几条混乱的世界当中。
这个世界却是重合在一起的,又是冷酷,分明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是对抗还是…只觉得眼皮下漆黑之中点点的金银花开花起来,努力要自己被带回以前的现实,人是可惜不能得到。
有点痛有点伤感,开始听到了孩子们的喧闹之声,把全身之力灌注到了脚上,想要用力的往下蹲,但没有动作,丝毫在关注到手上,仍没有丝毫的动弹,突然嘴角一阵麻痛,又有些经不住那移动的吱吱鸣叫的扯瓜,猛然从休克的状态恢复到人的世界,那嘴角的鲜血液口水连线的戛然而止。扭头看看背脚被潮湿和飞动的苍蝇,不觉是得拿断魂的,点点滴滴原来是黄粱噩梦。
上一篇:与子对语
下一篇:闲读《上善若水》之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