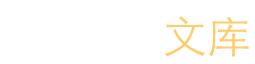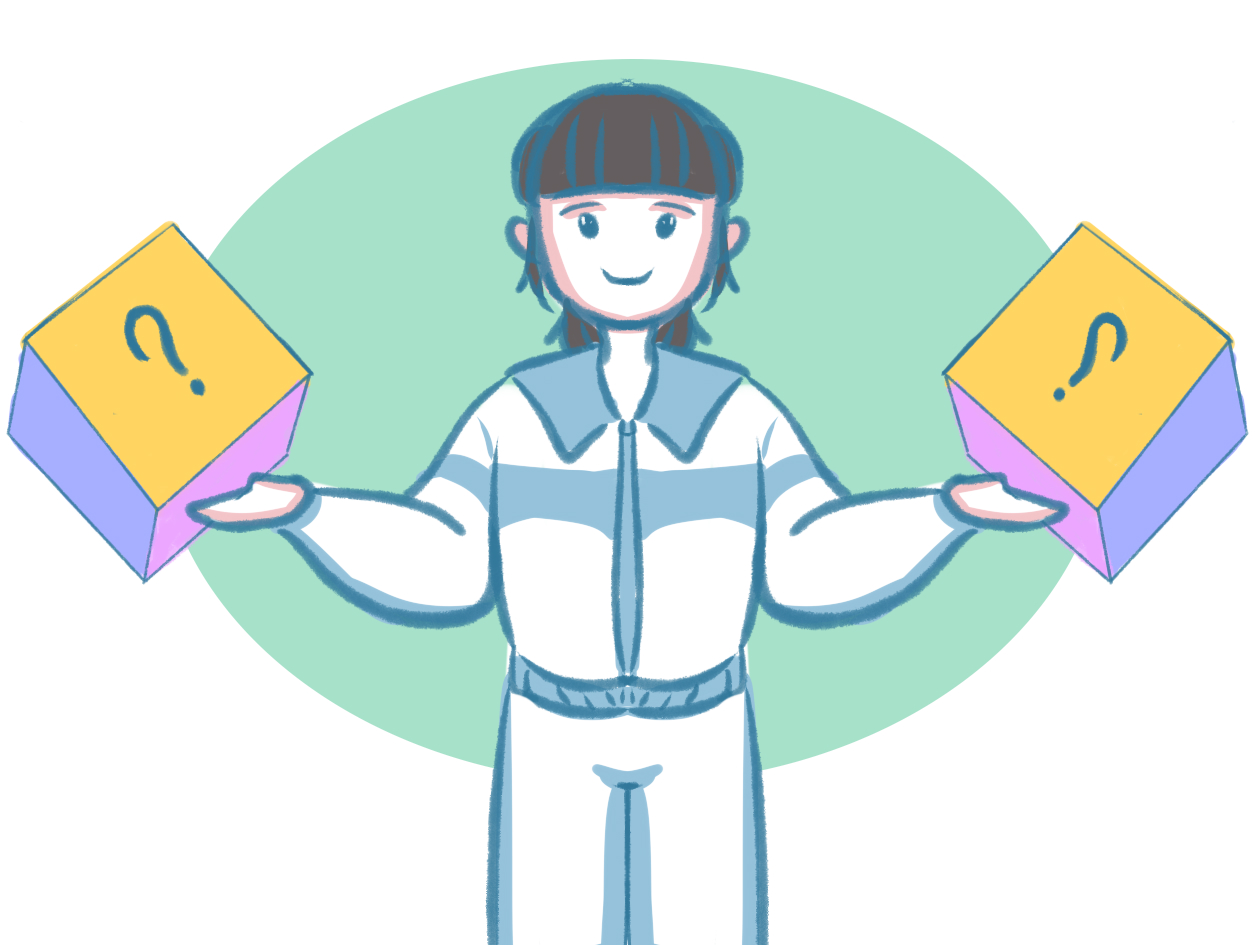一晃二十多年没在老家过年了。
今年春节,我终于觅得一个机会,可以在老年过一个踏踏实实的“年”了。
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年如期而至。凌晨三、四点,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就开始奏响,过了没半个小时则连成片,接着就汇成一体。
厨房里,母亲和二嫂已经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交响曲。
锅底下架着木柴,燃着熊熊烈火。鸡是自家养的鸡,抓来现杀的;鱼是昨天刚从塘里捞上来的;蔬菜是从菜园里拔的,香菜、青葱和紫苏也是自家种的。
——这样想着。一股鱼的腥味夹杂着稻柴的气息,“扑”一下进来,涌满了我的睡房。紧接着,大量投放的辣椒起了作用,腥还是腥,但却变得有些诱人。气味渐渐地厚起来了,起了浆似的。再接着,紫苏啊,香菜啊,青葱啊,一股脑下去,气味就像爆炸,蓬一下起来了,灌满房间的角角落落。
一瞬间,那相当丰富,层层叠叠,密密实实的气味,突然就柔和了,洋溢开了,那是添上水的缘故。
对了,应该是水煮鱼。小时候,一见到母亲做水煮鱼,我便垂涎欲滴。守在灶台边寸步不离,对其他小朋友的呼唤置之不理。所以,我曾怀疑自己是属猫的。
随后,又是菜籽油炸锅,香气四溅。渐渐的,气味就丰富了,似乎要拉开架势,大干一场。气味是一层一层过来的,红枣、菜籽油带着一股子冲劲,将各种气味打过来。这些气味在睡房里澎湃起伏。然后,渐渐地,渐渐地,那股子浓郁融化为清香,去除了肉的肥腻味,只剩下淡淡的香气了。
炖鸡,千真万确,就是炖鸡。没有那么多配料的杂味,但是,这炖鸡的香味却又要比记忆中的炖鸡浓厚多了。好像有什么力量,将这鸡的原味,突出了一把。是什么在起作用呢?再细循着那股炖鸡的香气找下去,我终于觉出了:他们在炖鸡里放了一只鳖。而且,一定是野生的鳖。于是,炖鸡的醇味潺潺地流淌过来,好像将那火爆劲夯实了,沉住了气,一点一点来。
炖鸡,是母亲的绝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它曾不知疲倦地给我以听觉、嗅觉、视觉的全面冲击,让我身上的所有味觉,细微至每一个毛孔都被它彻底地打开,让我尽情地享受这味觉的盛宴。这加了鳖的炖鸡,更是融入了浓浓的仪式感,给人以富足和尊贵的味道。是小康生活的气息,更有一种盛宴的味道,带有古意。
突然,冲过来一种熟悉的气味。这股子气味由弱渐强,转眼间,满屋都是。它带有一种涤荡的意思,将室内所有的浊气都熏灭了。整个清晨沉积下来的气味,被它扫得干干净净,使这肥厚起来的空气清新了一些,也爽利了一些。
——久违的香大蒜熏香。现在,我真的认可它的“香”了,或者,不叫香,叫“芬芳”, 大蒜的“芬芳”。
随后,腊肉的气味夹在大蒜的清香里,悄悄地进来了。它这么蹑着手脚跟进来,似乎带着些试探的意思,以为多年不闻不问,我把它给弄丢了。腊肉,湘北农家独特的加工工艺,那气味呀,就好象在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似的,唇齿之间,都是。细品,童年的味道,故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都在腊肉的香醇里。
后来,传进一股淡淡的米饭的焦味。显见得是饭熟了。它的香气是那么重,又那么稠,以致,香气就好像一咕噜,一咕噜地涌进睡房。米饭的焦味,有着一股子冲劲,倘若不是大锅大火地轰炸,是很难达到这种效果的。小时候,不管我藏在哪里,游戏结没结束,天一擦黑,烟囱里冒出烟来,一股米饭的焦味,就是游戏的终止符,我就会从甘蔗地里出来,从草垛里出来,从树上遛下来,顺着那焦味一一回到母亲身边。
开饭了。我打开那支存放了多年的53度飞天茅台酒,茅台酒的醇香便像脱缰的战马,带着一股子蹿劲,满屋子乱蹿,那叱咤风云的气势,有一种浮华的意思在里面,和农家的风格大相径庭。于是,屋里的香味就变得尖锐了,而且带着一种异端的气味。它飘在哪里似乎有些离题,可其实却是突出了主题。这些年,就因 “异端” 不断地渗进来,故乡农民的心态和生活追求才成了城市的山寨版。
餐桌上,我吃着母亲做的饭菜,感觉菜分子里满满都是故乡的味道,不断地唤醒我童年少年的记忆。我大口大口地享受着,幸福地告诉母亲:“妈,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饭,味道最可口的菜!”母亲那苍老的嘴角顿时露出灿烂的慈祥,她的声音笑了起来,她的动作笑了起来,她那刻满沧桑的脸上也挤进了许多微笑和温暖。我再抬头看看围桌而坐的亲人们,他们都沉浸在这股子年味里。
烟火最动人的地方也正于此,它将人的味蕾和情感悄悄连接起来,直至成为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