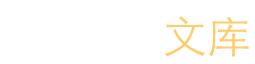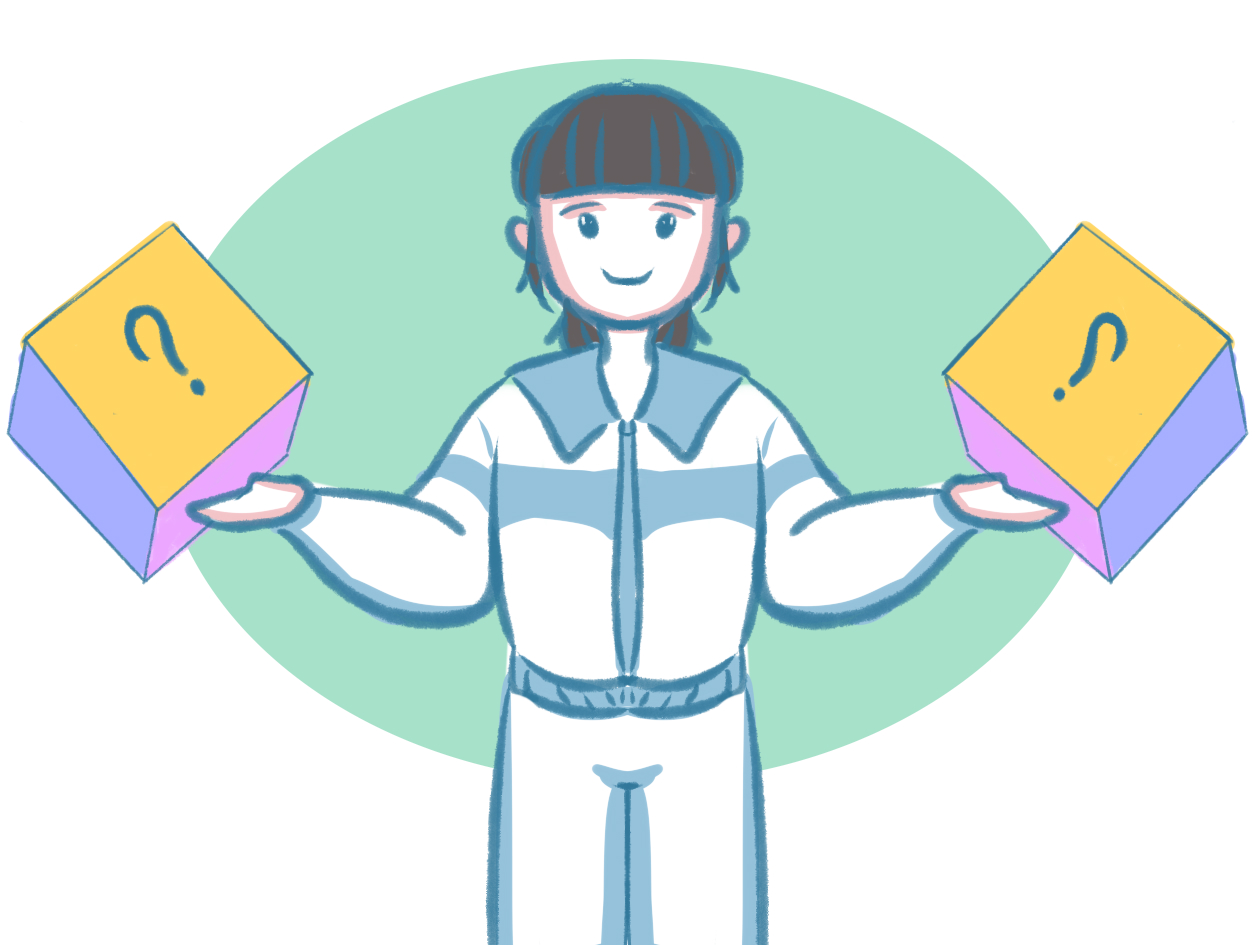从初中开始,我就离开了村子,到县城上学去了,也就在那一天,娘特意在村口的小路边栽了一棵柳树。每到星期五晚上,娘就守着小树傍,望着县城的方向,瞅着我一点点的由远及进、由小变大,快到跟前,娘兴奋地迎上去,取下书包,摸着我的头问寒问暖。到了星期天,娘又把我送到村口边的小树傍,看着我向县城的方向越走越远,由大变小,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虚点,她还在那里张望。
在娘的守望中,我就像一棵围绕着娘转动的卫星一样,一星期回归一次。
后来啊,我到外地上军校,每到寒暑假,娘总在村口的柳树傍,望着那条小路,远远处走来一个身穿军装的年青人提着箱子,看着我如期而至,娘无比的激动,催着我:
“再回来的时候,给娘带一个媳妇回来,村里象你这么大的娃都抱孩子啦。”
在娘的守望中,我这棵卫星的轨道飞远了,变成了半年才回归一次。
就这样,娘一年年在村口望着,树也一天天的长粗,变成了参天大树。
后来,我果然带了外乡的媳妇回家了,也是从那以后,我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可娘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村口的村傍望着,有时候望了一天没有见人,她就会自言自语地叹息道:
“娃‘今个’没来,可能‘明个’就会到了。”
在娘的守望中,我这棵卫星回归的周期无限延长,留下的是娘在村口的柳树下望眼欲穿。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春去秋来,她的心里都守着那棵老柳树……从一头青丝望到满头白发。
娘在村口柳树下望着远方等呀,盼呀!那是怎样的心路啊?那是一棵由满怀希望的火热的心到凉至脚底的失望;那是让我一想起来就为之落泪的叹息;那是沉重得让我今生今世永远无法还清的、回家的债。哎,娘,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您才真切地体会其中的滋味呀。
再次回家的时候,是我、媳妇和儿子一起回的。娘一接到电话,就匆匆忙忙地来到那棵老柳树下。远远的,见到三个人出现在娘的视线里,她近乎跑也似的急走过来,一下子就把我的儿子搂在怀里:“来孙子,你可想死奶奶了,让奶奶看看!”
回过头来,却嗔怪着我:“工作这么忙,打个电话就行了,大老远的,还回来看啥,多耽误工作呀。”
娘虽这么说着,却掩饰不住期盼已久的高兴,满脸的折子笑得叠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细线,从脸上笑到心里。那是一条条小小的丝带,娘用皱纹轻轻系住,想把儿子栓住,就像当年系住风筝的那根线一样。
我突然发现,娘怎么老成了这个样子。什么时候开始,娘那光滑红润脸变成了灰色的核桃皮,什么时候开始,娘的一头乌发爬满了灰白色。那日复一复地盼呀,日复一日地等呀,把娘都盼老了。
那年,娘病得很重,接到信,我的泪不由自主地滚落着,一种莫名的不祥之感,让我心慌意乱。
病重的娘叫我把她抬到村口的柳树傍,指着村子的后山说:
“儿呀,这次娘恐怕不行了,你看……那山坡上最高的山包吗……就把我埋在那儿……那儿高……你们啥时候回来……我都能看见……”
我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哽咽着对娘说:娘……没事的,咱明天就到大城市去看……不行就到北京、上海……你会好的。
不了……娘自己的病自己知道,别白花了那冤枉钱……
娘下葬的那天,我长跪于娘的坟前,哭得昏天地暗,几乎背过气去。 “是我呀,是我这个不孝子害了娘了呀。”子欲孝而亲不在。鼻涕和泪都混流下来,我不能自已……
娘,自从您把我送出村口的那一天。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您那棵思儿的心,却越来越强,越老越切。您在病床上,嘴里念得都是儿子,直到你临死的时候,还在念着儿子呀。而我呢,只是在您死之后才知道这些。娘,您是带着念儿的失落走的呀,可我,又怎样像你解释呢,我有满肚的话呀,我多想……我多想……可是您却躺在了冰冷的地下,转眼之间,你我成了阴阳相隔的两界。
娘去世后,村口的那棵老柳树再也见不到娘没日没夜地盼儿子回家的孤独与失望的身影。不什么原因,在娘死后的第二年,那棵老柳树干枯了。也许,因为长时间的守望,那棵老柳树已经有了灵性,它是随娘一起去了吧?
这以后,每到清明节,走到村子口的老柳树所在的位置,我远远的看到娘的坟头,恍惚间,那坟头就是娘的眼睛,她在那里望着她的儿子和孙子回来呢……
可如今,儿子又重复着我当年的故事,幼儿园时,儿子只顾着缠着你,让抱着,让背着;睡觉时,他光着屁股钻进你的怀里,他和你的距离是零;上了小学,他不安份地站在你自行车的后座上,搂着你的脖子,虽说同样是贴在一起,但却比躺在怀里,终究是远了些;上了初中,不用再接送了,当你感觉轻松的同时,却发现离儿子的距离远了许多;到了高中,上了大学了,更是越来越远。当你把儿子送到车站,看着他向检票口走去,直到身影渐渐地消失,然后随车一起渐渐地越走越远,站台上,只留下空空的铁轨……那种怅然若失,那种瞻前顾后,那种人走后的清冷,那种清冷时的回忆,和娘在村口目送我走远是何等的相似。
此事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儿子的经历虽然没有我和娘这般道凄苦,实质上却一样的。人,长得越大,离母亲的距离越远,最后变成见一眼孩子,都是一种奢望。这是生命的轮回么,这是上天的约定么,这是自然规律么?我不得而知,也真得不想找到这个答案。
小时候,我和娘一起放风筝,看着那高高飘在空中的风筝,我好奇地问:“娘,那风筝为什么不飞走呀?”
“因为,他有线呀,风筝有线握在娘手里,他就飞不走了,飞得再远也要回到娘的身边。”
哦,我若有所思地望着空中的风筝……一阵风吹来,把线吹断了,那风筝向着遥远的地方飞去,由一个大的身影变成了一小点,最后竟一点也不见了。我哭着要娘找回那可爱的风筝,娘一直找了一个时辰,最后,才在很远的一棵柳树上找到飘落的风筝,用一根长棍子够了下来。
娘在身旁告诉我:“孩呀,风筝千万不能断了线,断了线就从娘身边丢了!”
人一来到这个世上,注定要像风筝一样,飞得越高就离母亲越来越远,谁也逃不出这个定数,直到你也老了,叶落归根,守着母亲的坟傍,那根就是故乡,那根就是母亲。等你哭天抢地地看着父母已经到了地下,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根的孩子,没有线的风筝,一下子觉得自己是那么可怜,自己老的速度便出奇的快,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小时候,
回家是村口的那棵柳树,
我在树梢,母亲在树根。
后来啊,
回家是后山上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我在外头,母亲……在坟墓的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