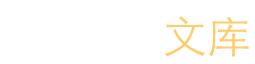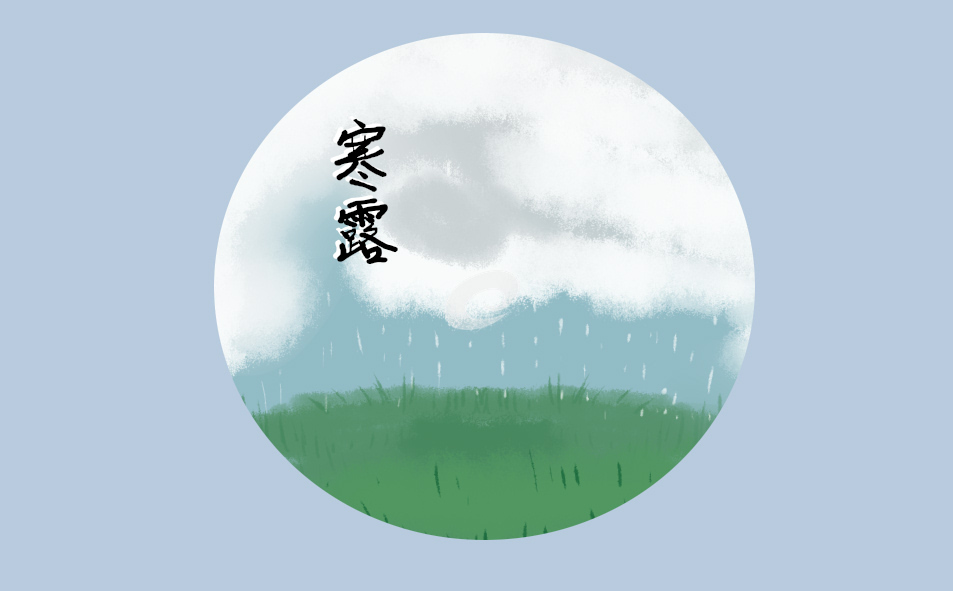那时我们村的果树并不多,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在村子里闲窜,对村子里的果树了如指掌。算起来还算数枣树居多。能称为“枣树之王”的大概要数我大伯家门前的那颗歪脖枣树。听说歪脖枣树是我老爷年轻的时候栽下的,大约有百十年的历史了。树不算高,足有腰那么粗。每年能打枣上百斤。从枣树开花开始,我们一直盯到青枣变红。
有一年六月底,突然狂风大作,倾刻间青枣般大的冰雹便下起来了。冰雹过后,我们到外边拣冰雹玩,发现大伯的女儿萍姐正在拣地下的枣。我们就像发现了宝库一样兴奋,连忙弯腰拣枣往嘴里送。比我们年长几岁的萍姐说:“生瓜梨枣吃吃不得了。”我不以为然地说:“不好吃你还拣?骗人哩。”萍姐说:“拿回去煮熟再吃。青枣吃多了还要拉肚子。”我听了半信半疑。也有的伙伴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拣起来就往嘴里送,结果不等晚上就嚷着肚子疼。我将拣来的两口袋枣拿回去,母亲把它洗干净,放在锅里煮。煮熟的青枣虽不太甜,但又面又软也很好吃。
俗语说:“七月十五枣红脸,八月十五枣落竿。”一到七月,我们便开始偷袭大伯家的枣树。为了防止我们几个顽皮童,大伯在枣树干上抹了一层牛粪,谁也不敢再往树上爬了。不过我们有别的办法,那就是用竹竿乱打一气。时间一长,枣树低处的枣就被我们消灭光了,只剩下高处的枣在太阳下红着脸笑。后来我们想出办法,用瓦片、小石头打枣。远远地站着,拿起一个小瓦片使足力气“啪”地打过去,有时能落下几个枣。但终因我们力气有限,每次大动干戈也打不下几个枣。倒是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几个大孩子打枣时,因为我们小跑得快,能拾不少枣吃。所以一逢到大孩子路过,我们主动给他送瓦片石块让他打,我们则做好冲过去拾枣的准备。悲剧也就是出在拾枣上。
午饭后的一天,大人们午休,我们在村里转悠,走到离大伯家不远的河边,脱了鞋准备下去洗澡的时候,看到灰子哥在弯腰拣瓦片准备打枣。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小伙伴仪娃就像勇敢的战士一样奔了过去。只听“哎哟”一声,仪娃抱头蹲在地上。灰子哥扔的石头不偏不倚,正打在仪娃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灰子哥也吓愣了。我们一边叫着:“仪娃流血了。”一边跑到他家报信。仪娃的奶奶正在纺花。听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的汇报,便扔下纺花车,一边哭一边往出事的地点跑。她抱着仪娃,大声哭着喊着:“我的小乖乖呀,这可咋办呢?”仪娃爹在外谋生,他的妈妈还在家里照顾他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小妹妹。按在农村的规矩,不足月的女人是不能出门的。他奶奶只有哭的份了。我大伯不知从什么地方才回来。见此情景,忙抱起仪娃朝村卫生所跑去。他奶奶踮着小脚在后面哭着撵着。我们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会,也跟着他们往卫生所跑。等我们赶到卫生所的时候,仪娃正坐在凳子上喝红糖茶。他头上缠了一圈白布,有隐约的血迹,就像《地道战》中被敌人打伤的解放军战士。看到我们,他低下了头,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
自从仪娃拾枣被砸以后,大人们便教训我们说:“你们再去打枣,就会像仪娃一样被打个冒烟洞。”也有的说:“看看仪娃,后脑勺上那么大一块疤,将来连花妞也找不来。”果然 我们再也不敢去打枣了。
转眼间就到了八月。八月十四的下午大娘到几家近门交代要卸枣了,请我们大人小孩拿上筐、布袋去拾枣。我和弟弟都高兴起来,跟着母亲去拾枣。大伯的儿子青哥正坐在枣树枝上。他正在往嘴里送枣。待他吃美了,大喊一声:“卸枣喽。”便使劲地摇枣树枝。顿时枣儿像下雨一样砸下来。没有人感到痛,都蹲在地上抢着、拣着、笑着。弟弟是个好显摆的小孩子。他拣的枣不往母亲的筐里放,而是装在口袋里。待口装得鼓鼓的,他再弯腰拣枣时,枣便都从他的口袋里跑了出来。等他发觉时,就跺着脚躺在地下大哭大闹起来。树上的青哥也停了下,待大娘把自己的小针线筐拿出来给他,又把他洒在地上的枣都拾到小针线筐里以后,他这才高兴起来。青哥又开始摇树枝了。枣儿又欢蹦乱跳起来。有的还落在弟弟的小筐里,他顿时手舞足蹈起来。约模有一顿饭工夫,卸枣任务便完成了。大家提着满满的一筐枣,说说笑笑回家去。
母亲除了限量让我们吃枣外,把其余的都晒在院子里的古桌上,等晒干以后,春节做枣馍吃。当我再路过大伯家时,看到有几个没有被打下来的枣依然挂在高高的树枝上,个个笑红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