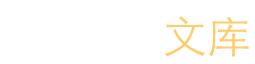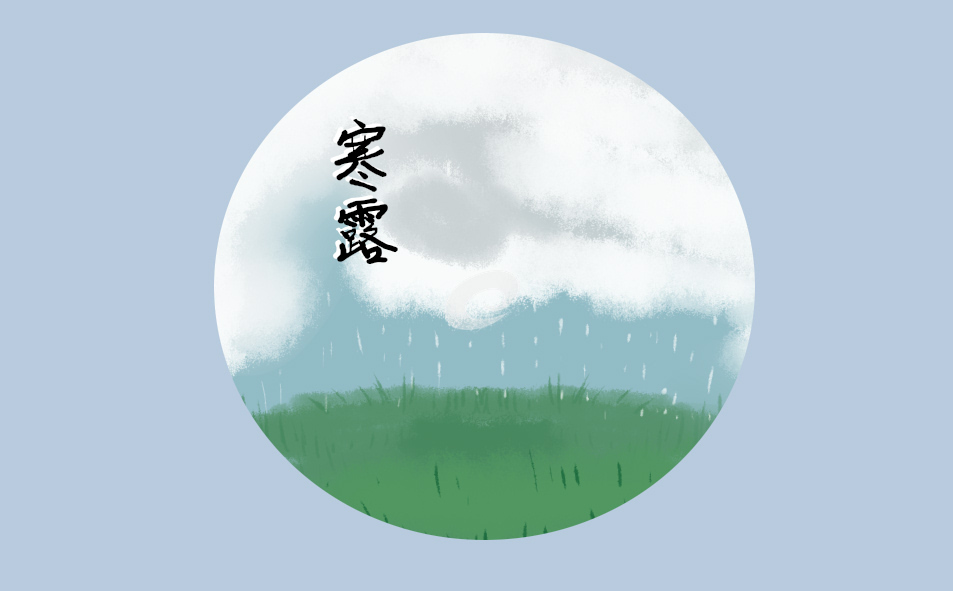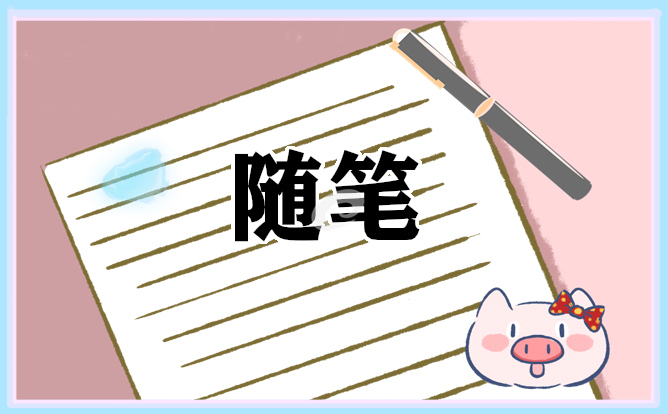投稿作者:刘显刚
题记:生活的河流暗潮汹涌,它会在不经意间带走你所珍爱的……谨以本文献给仙逝的伯父。
提纲:
1. 引子
2. 猝然辞世
3. 孤独的处士
4. 体制内体制外
5. 孝子典范与传统情结
6. 愤懑的酒仙
7. 两代人的对话
8. 乡土余绪
引子
公元2003年9月25日,注定是一个让我永远心痛的日子。这是一个阴天的午后,当家乡的大多数人依照固定的程式和生活逻辑奔波着的时候,一个孤独的高大的身影倒下了,倒在村前东向的沟塘边,倒在他为稻粱谋而日日往来的杂石路上:头发凌乱,脸色铁青,牙关紧咬,衣衫破旧,身子稍微呈蜷伏状,渐呈衰势的肢体骨节突兀,青筋暴出……路人发见他的时候,他的肢体已然冰凉,只是右手仍紧紧攥着一只开了盖的酒瓶,身上似乎还有一股酒气。当我三个多月后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赶回来的时候,那曾经伟岸的躯体已经与乡土相融,唯一可辨识的,是那村野里的孤坟:一堆夹杂着几块青砖的黄土。他,就是我的伯父——刘庆海 。
猝然辞世
海伯的死,对于周围的乡亲邻人来说,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作为一个没落的“乡绅”。他终日以酒释怀的声名早已成为四邻有趣或无趣的谈资;而他的猝死,也不过是为一个话题、一种现象提供一个结局和终止品评的现实原因罢了,仅此而已。时间永是流逝,现在不断地成为历史,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到即使在最最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上也搜索不到他的名字的小人物就这样去了,不曾留下些许的墨迹与豪言壮语,高亢浑厚的声音也早已消融在空气里。但是,作为一个生命,他又毕竟是特殊的,乡愿芸芸,我们终究没有权利去斥责他的平凡甚或庸碌。更何况,从近半个世纪以来乡土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历史背景出发,海伯的平生遭际又是那么典型的悲剧性个案。
无论如何,海伯的死都是突然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公众中高大、魁梧、硬朗、豪爽与倔强的一贯形象,而且也与乡村传统的“负重”型生活观密切相联 。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探知海伯临终时的心理,更无法明晰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的思绪。他是在酒精的麻醉中带着无尽的心痛与遗憾走的吗?抑或是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彻大悟,安然西去?我们不得而知。那具乡邻发见时已然僵冷的躯体留下了一个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那座村野里的孤坟除了寄存和留驻下亲人的几滴伤心的眼泪和无尽的哀思之外已经没有更为明确的现世意义。然而,尽管一切的一切在乡村农人的口碑中似乎早已盖棺定论:那是一个潦倒酒鬼的自然而然的下场;尽管笔者出于专业的敏感曾经强烈的怀疑过海伯手中那瓶劣质白酒的可食用性 ,但是,海伯去了,永远地去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事实是如此的残酷以至于无论是闲人们以讹传讹的评议还是关于死因的任何一种善意的情绪化的怀疑都已无谓,都已虚妄。一介书生,不肖阿侄,我也只能在垂泪中喟叹造化的无常,在这漫漫冬夜,在这岁末的寒冷的空气里,摊开稿卷,录下神思,既缅怀猝然辞世的海伯,也借此机会反照乡村的现世生活,写下关乎乡土人生的一孔之见。
孤独的处士
虽然,没能在临终前与海伯相见是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至少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海伯一直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孤独之中。那种夹杂着浓厚的失意情绪的孤独感时时在考验着他的耐性,向他的理智进行着强有力的挑战。这一点,从他那习惯性的酗酒、日益暴烈和反复无常的脾性以及日渐增多的自言自语式的牢骚中可以窥见一斑。
孤独之于海伯,不仅仅是外观上的形单影只,更是一种源于对生活无比深刻的内心体察的持续性的心理状态。他有家,但家的温馨却因为生活的日渐困顿和子女求学婚姻诸问题的长期困扰而荡然无存;他有事业,但所谓的事业所能带来的荣耀和成就感也早已随着公社体制的解体和他本人的“失业”而变成明日黄花;他有朋友,但那些曾经因利益的诉求而与之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朋友们也已经弃他而去。于是,他彻底地孤独了。日常度支上的捉襟见肘与生活视野的相对闭塞滋长了他的失意情绪;对现世社会尤其官场之林林总总的“看不惯”或者说是一种由体制的失意而引发的源于个人性格的情绪反应又使他从根本上缺乏面对纯粹农人生活的勇气。更何况,这种面对还伴随着个人耕作技能、劳力、生产资料的缺乏以及传统农业因为体制性的调整所产生的阶段性整体性的不景气。
当然,从历史观,海伯在后期岁月中所面对的生活范式转型的尴尬处境亦非偶然,它只是乡土中国体制变革与现代化演进中的一种个体反应罢了。但是,海伯并非是一个超然于历史的哲人,他早年受到的富于革命激情和政治理想主义色彩的“红色教育”和多半来自经验的生活感知使他不可能在面对现世生活的挫折时抽象出一种更为圆通的生活哲学,而不陷入一种在我看来是必然的“孤独”之中。于是,在淮河之间北部的这个被称为“小刘郢子”的村落里,炙热的骄阳下,落日的余晖中,连绵的雨水里,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他那高大的、孤独的、倔强的身影,或在田间劳作,或在户外伫立,或者干脆在自家的平房上漫无目的的踱行。现实的遭际令他孤独,他似乎也慢慢“习惯”了这种孤独,“享受”着这种孤独。于是,在四邻的一般印象中,他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孤独处士。
体制内体制外
海伯一生的悲剧,除了个人性格与乡村传统层面的原因之外,直接的触因却是中年后期生活范式的强制转型。一如前述,海伯曾经是一个名动乡野的“人民公社”干部,依凭士子的传统赤诚和继受自官方的红色信仰,海伯在公社干部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同时,与一般意义上的体制内官僚相比照,海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一种政治上的足够圆通和灵活原则导引下的功利思维,因为他曾相当剧烈地批判和抵触过谄媚之风并似乎成功地保持了一己道义和法理上的廉洁 。
明晰海伯在体制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应该是重要的,它对于我们探讨乃至理解海伯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所发生的心理异变、个性扭曲及至最终的猝死悲剧都具有显明的意义。概而言之,海伯“体制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大致可以用“原则性的操守、适度的入世和有限的通达”来予以描述。这种基源于事实的学理概括所试图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息:作为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红卫兵一代,海伯在体制内的生活中已经被迫面对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的紧张冲突,并不断在原则性的操守与体制性的功利之间展开着内在和外在的博弈与调和。对现实社会之体制的认同乃至融入似乎必然要付出一己之生活旨趣、思维进路、固有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成本”。而这种成本的“支出”,因其与个体的本位性的生命意识相关涉,故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个体的半强制性的“社会”化、庸俗化为预设背景,而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量的变化。
作为红卫兵一代,时代赋予了海伯太多太多的纠葛、苦难、冲突与幻想:他接受的是充溢着革命激情的红色教育,领导人语录和各种各样“左”的政策、纲领、路线、思想烂熟于胸,(尤其在青壮年时期)他脑中经常浮现的是本土色彩浓郁的多半源于官方宣传的完美的共产图幕;而另一方面,他又出生和生长在乡村,在不知不觉中浸淫了太多太多的乡土意识和传统思维。这样,当我试图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去反观海伯对体制的认同、融入及至最后失意的离开这一系列的过程时,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存于一己的冲突的价值观和近乎分裂的双重人格。终其一生,海伯在心灵猛烈震荡与内在价值取向的无尽冲突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泥里打滚的野小子,富于激情的革命青年,名动乡野、魄力十足的人民公社干部……他是依凭怎样的一种心理资源来完成这一系列的角色转换的呢?家族图腾抑或是社会信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确乎已经是一个失意的酒徒,一个失败的父亲和一个无比孤独的处士,一个彻彻底底的体制之外的农人。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悖论。当他经由一系列的嬗变而最终“适应”了这种体制内的生活时,体制却又无情地抛弃了他。这样,内心长期积存的失落感加之生活范式被迫转型所带来的惶恐使得接近知天命之年的海伯手足无措:他根本没有为即将到来的体制外的生活——纯粹的农人生活做好准备。于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持续性的酗酒、失意性的愤懑、巨大的无以遣怀的孤独和不得不面对的整个家庭的惨淡经营。
孝子典范与传统情结
或许,早年所受到的红色教育已经为海伯提供了一种令他可以超然于乡土哲学和传统思维的生活逻辑。但是实际上,舶来的信仰并没有切断他与厚重的乡村传统的联系,反而可能从反面加强了这种联系。这一点,从海伯对于人子之孝的极力尊崇和近乎夸张的身体力行中可以窥见一斑。四近的乡邻可能对于海伯生平的某些方面尤其他后来由失意而酗酒的行端有所非议,但是,他们却都近乎一致的肯认他的孝心孝行。海伯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他对父母的尽孝是真诚的,毫不做作的,不遗余力的;而且他的这样一种人子之德还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放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他对几乎所有的乡邻长辈的关心与尊重。时至今日,每当我那年迈的祖父母老眼含泪的追忆他们的长子生前治孝的种种行状时,总有几个一般年纪的老人家在旁“附和”,那情形,就好像一场集体性的忆苦思甜。
当然,单纯意义上的孝并不能为乡村传统之于海伯的深刻影响提供充分的佐证,因为人子之孝同时也是新社会里为官方所肯认并大力加以提倡的家庭美德。但是,平日里只言片语的交流加上与海伯有限的几次较为细致的谈话,再结合他那强烈的常常外化的宗族意识和祖制人伦观念,一切就相当的明晰了:海伯有着浓郁的传统气息,在他身上体现着根深蒂固的乡村传统,一种深深扎根于土地的人生信仰。而这种乡土意识正构成了海伯“冲突的价值观和近乎分裂的双重人格”的一面。
可以说,终其一生,海伯都没有摆脱乡土意识与共产图幕的近于对立的内在纠缠,这给他造成了长时间的压抑和内心苦痛。舶来的信仰曾经给他带来体制内的荣耀,对于乡村传统的不经意间完成的忠实继受和坚定认同又在事实上为他的乡土人生找寻到了一种可供凭靠的精神归宿。然而,当体制及由其所带来的成就感与现实利益最终都离他而去的时候,当他的生活再次与土地紧紧绑在一起的时候,他终于在心中把乡土哲学定为“一尊”,而与他曾经长相厮守的共产图幕渐行渐远了。
愤懑的酒仙
海伯是因酒而亡的。尽管由体制变异所引发的失意情绪以及相关联的生活范式的强制转型所带来的的巨大的挫折感很可能是海伯生命后期潦倒生活的主要触因,但是酒毕竟在海伯悲剧式的猝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失意者几乎总是特别钟情于那可以麻醉他们小脑的酒精。他们借助它就可以暂别烦人的现世生活,在朦胧与飘忽中保持那份生命的激情与执著。于海伯而言,当他身处体制之内时,酒是迎来送往、交流联谊的必需品,他一定也是在这时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并在各种各样的应酬中培厚了之于饮酒行为本身的自在与优越意识。而当“不幸沦落”为一个体制之外的道地的潦倒的农人时,他竟没有放下酒杯,反而由一般需要发展到嗜酒如命直至最后因酒而亡。海伯对于酒的这种持续的甚至是变本加厉的喜好,在我看来,除了长期饮酒所产生的病态的生理需求(酒瘾)外,应该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心理层面的原因:泛泛说来,经由酒精的麻醉他可以“暂别烦人的现世生活,在朦胧与飘忽中保持那份生命的激情与执著”;微而言之,曾经无数次麻醉他的道德自省意识从而使他的体制内的生活得以“心安理得”的酒精在他为体制所抛弃并陷入穷困潦倒、一筹莫展的境地的时候并没有“冷落”他,更没有“嘲笑”他,反而一如既往地为他营造着一片现实泥淖中的难得的宁静,这本身就已经使他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宠信”那弥漫着刺人的火辣辣的香气的白色透明液体。更何况,这种“宠信”虽然容易遭人非议,但却是沉浸在巨大的失意情绪中的海伯发泄郁结于心的苦闷与生命激情的绝佳径途。
这里必须提及,酗酒行为其实并未减轻海伯内心的苦痛,反而使担了“酒鬼”声名的海伯面对现世的生活时愈加地凄凉孤苦,愈加地偏激愤懑。但是,酒精似乎已融入了他的血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经完全离不开酒了,酒确乎已经成为他完整生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尽管海伯在四邻宗亲的苦口婆心的规劝下曾经不止一次的试图戒酒,并且我所知道的其中一次似乎还颇有成效 。但是,当噩耗传来,我终于明白海伯至死也没有摆脱酒虫的折磨。
或许,老来失意的海伯自己也不会想到,他会带着无尽的遗憾而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时候遁离红尘,而且走时满身的酒气,一只手中还紧紧握着酒瓶!丢下年迈的双亲,抛下依然为着生计而一筹莫展的妻儿,愤懑的酒仙“飞天”而去,那座曾经气派的宅院愈发显得冷清了……
两代人的对话
前已述及,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海伯与我仅仅进行过有限几次较为细致的谈话。虽名曰“谈话”,其实际的表现样态却是一方持续性的近似呓语的亢奋和另一方形式主义的漫不经心的附和。如果说海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乡村群体人格,那么海伯与我的这种为数不多的交流其实是乡土社群与刚刚走出乡村的异化的个体之间的生命对话。尽管我对海伯怀有充分的敬意,对这种代际的交流也满怀憧憬,但是,结果却遗憾的证明: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代际生活哲学的碰撞 。以历史观,海伯与我的这样一种代际的隔膜其实又是一种传统思维和现代意识的交锋。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悖论:在强势的官方意识形态熏陶下的海伯曾经颇具现代感,他的一生也曾长久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而最后,当他的侄子(我)循着现行的教育体制走出乡村、走进现代城市的时候,他竟作为乡村传统的代言人而出现在我的面前,进行多半是一厢情愿的训导 。
海伯在亢奋中的谈话大多涉及他的早年故事,诸如少年求学的传奇经历等等,当然,最令他感怀的还是那段作为红卫兵而进京串联的日子。然而奇怪的是,海伯对于他青年时代后期所开始的体制内的生活却很少提及,我猜想,个中缘由一方面与其强烈的失意情绪相涉,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所产生的巨大的精神落差也在客观上迫使其采取了审慎的回避态度(虽然海伯极有可能在进行着不间断地内在反省)。
必须指出,代际生活观的隔膜以及由此引发的价值诉求上的差异让我与海伯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交流变得异常艰难——他和他们希望我忠实地继受下乡土传统,经由文凭的保障而“入朝为仕”,成为一个光耀门楣、支撑门户的体制内的官僚 。而我呢,尽管并不拒斥乡土哲学甚至并不认为乡土文化传统本身具有可非难性,但是,我却无法完成对之的“忠实”继受;与此同时,由于我对从政为官的兴趣远未及对作为一个具有公共关怀的秉持“良知的傲慢”的知识分子的兴趣,因此,我也无法接受他和他们所给予我的人生“路线图”。这样,自然而然,海伯与我之间展开的这种两代人的对话的事实情态是一方呓语式的亢奋和另一方的漫不经心。
真的,直到今天,每当我抬起头来遥望那座村野中的孤坟、更多地在精神层面上缅怀逝去的海伯时,我仍然在试图用我之生活哲学与话语逻辑来对海伯那独特的悲情的乡土人生进行解读。而这篇稚嫩的文字或许正是我与海伯的另一种形式的“代际对话”吧。希望,它不是我一厢情愿的呓语;也希望,它不曾过度地惊扰海伯那已然安睡的乡魂!
乡土余绪
海伯的人生透着浓厚的乡土底色,他的潜在的或显明的意识形态、生活哲学、价值取向等等都打上了永远涂抹不掉的乡村徽记。尽管酗酒而亡的终了结局以及曾经长时间脱离劳动的经历使他的乡土人生多少显得不那么纯粹和典型,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海伯所代表的是一代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红色教育”,亲身参与过为数不少的政治运动,后来又依凭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而融入了体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20世纪后期的体制变革与现代化演进中迫于客观情势而淡出了体制,变得日趋保守甚或落伍(如海伯),另一些人则依然顽强地在体制中“与时俱进”,进行着突围色彩浓厚的近乎悲壮的努力。作为理性主义色彩浓厚的红卫兵一代,无论程度如何,他们身上都(至少在一定时期)存在着传统性与现代感的矛盾命题,无论他们最后所皈依的是民间的传统(其主体部分当是乡土传统)还是体制内的现代。
最近的风特别大,因此扬尘也多,我的稿卷也落上了薄薄的一层黄土。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海伯的亡灵之于我的回应,但是,我必须在此打住了。或许,逝去的一切只有在历史的理性反照中才能凸现其现世意义,一如今天我对海伯的追思。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今天的追缅不曾过度地惊扰那已然安睡的乡魂!安息吧,我的海伯!
2004年1月于淮南-碌芸居
笔者注:这是一篇关于 乡土人生的文字,是笔者 在寒假 省亲时有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