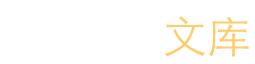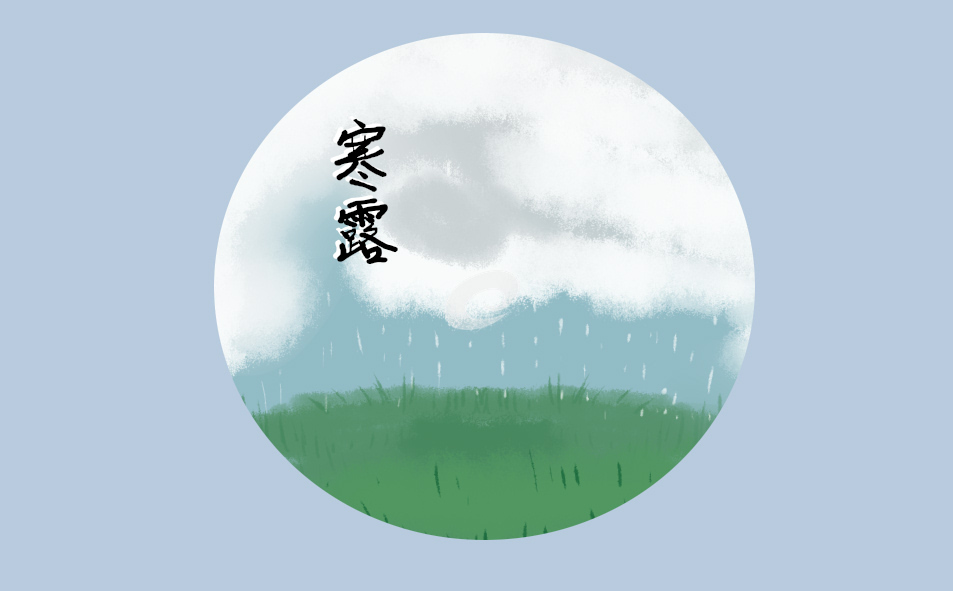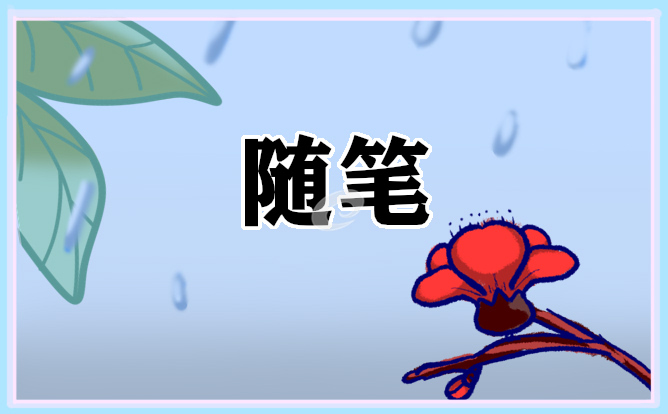梧桐的浪漫,雨珠的柔美,她们的完美结合,让南京人对梧桐有了更多的眷恋和怀旧。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关于生活随笔_南京的梧桐雨,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生活随笔_南京的梧桐雨(一)
有一部电视剧叫《梧桐雨》,故事经典,耐人寻味,好看的很;有一首歌曲,也叫《梧桐雨》,词曲都很优美,真乃好听至极,歌中唱到,又是秋夜点点梧桐雨,恰似离人悄悄在哭泣,想当年,我和你,心相映,影不离,如今的你又在哪里……
南京的四季,处处梧桐,处处梧桐雨,尤其到了初夏,潇潇洒洒的梧桐絮整日纷纷扬扬,宛如天女散花,又似漫天飞雪,有人烦它,也有人爱它。如果到了淅淅沥沥的雨季,细细的丝雨暂时不能直接落到地上,那如扇状的片片梧桐叶先是将雨水接住了,然后再由它们将雨水洒落下来。看着那些参差不齐、大小不一的雨珠,仿佛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梧桐叶下的,清新的空气中更是飘散着梧桐叶的芳香。
南京人尤爱梧桐、梅花和香樟,对梧桐的感情更是没有任何的瑕疵。据说,南京广栽梧桐是在1920年,缘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如今,梧桐树真是给南京带来了太多、太深的美好和记忆,也成为南京一张响亮的名片。它们不仅绿化了城市、净化了空气,在夏日里,更给人们带来了珍贵的清凉。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在接近四十度的高温下,街面被烈日晒得能烤熟鸡蛋,而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的枝条和树叶相互交织在一起,能把几十米宽的街路上方遮蔽得严严实实,犹如一把把厚厚实实的帆布伞。这时,你若骑着单车,或步行在梧桐树下,会觉着特别的凉爽、舒适,心里也许还有一份小小的得意。
梧桐的浪漫,雨珠的柔美,她们的完美结合,让南京人对梧桐有了更多的眷恋和怀旧。不过,有时候也给人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期待,梧桐雨代表着遐想,代表着相思!南京的一位故友移民去了加拿大,最难以割舍的就是南京的梧桐雨,他还特意请我邮几片今年的梧桐叶过去,以解他对南京的爱恋。
我家的小区里也有一棵老大的梧桐树,直径将近一米,夏日的时候,邻居喜欢在树下放一张圆桌和几张板凳,傍晚时分,大家总是相约在树下喝茶、聊天、掼蛋。有时候,看着人家的清闲,心里会有许些莫名的羡慕和哀伤,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同周围的人说说闹闹,却忽而觉得自己异常的寂寞和孤独;有时候,独自傻傻的坐在梧桐树下,会觉得自己是个被世界遗忘的人;有时候,自己不知不觉便仰慕起这棵自由自在的梧桐树来……不过,还是高兴的日子更多,看着这棵高高大大的梧桐,遥想起远方那片不见日月的密林,我的心里突然很阳光、很幸福!
瞧,又下雨了,看见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兴奋地站在梧桐树下淋雨,突然妒忌起他们来。要是我和他们一般大,要是我也能和他们一起游戏,那该多好!原来,自己已经在梧桐雨中悄悄长大了……
有一次,我给孩子们上课,说起南京的梧桐雨时,竟然有些伤感!不料,一个孩子说,“老师,您听说过糖果雨吗?五颜六色的,香香的,甜甜的……还有玫瑰雨、花瓣雨、心雨……”他一连串说了那么多,说的我心都醉了。
淡淡的梧桐雨声,伴着淡淡的心情,也蛮不错。人的一生,平淡最好,激烈的事物容易让人倦累,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是呀,到了一定时候,人就会感到疲倦,觉着心累,只想看淡一切,静静的品一杯浓浓的香茶,坐在小雨沙沙的梧桐树下,淡淡的听一段轻音乐,比如《回家》,比如《春江花月夜》,比如《江河水》,比如《梁祝》,比如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在弥漫梧桐雨的夜色中,我们该好好歇息了。明天的早晨,还有忙不完的事等我去做,不能停息,永无尽头,所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站在梧桐树下,不禁感慨万千,人生的路总是太长,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梧桐树为我们遮风挡雨,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梧桐雨下的浪漫,好好走路,好好做人,好好生活,你的人生就会永远都在“好好”中安安稳稳地度过……(作者简介:黄宏宣,男,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东方作家创作中心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三级创作员,在各类刊物、网站上发表作品三千余篇,十多篇散文在各级评比中获奖,并出版散文集《我这十年》和长篇小说《深深叹息》)
关于生活随笔_纪念逝去的青丝(二)
“哎呀!九满,你有白发了!”话音刚落,妻子拨开我稠密的发丝,将我头上那根躲来藏去的白发连根拔起,摊到我的掌心。看她那神态,看她那表情,就象犯罪分子销毁犯罪证据一般惊恐、慌乱,所以,在她将那根白发毁尸灭迹之后,居然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此,她一有空,就在我柔软洒脱的黑发中寻找异类,每每发现一根白发,她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溅起一片响亮的欢呼!她很像一个农夫,依靠铲除杂草来保护庄稼的生长,让她年轻的丈夫拥有一头漂亮的青丝。
那时候,我刚跨过三十岁的门槛,雄姿英发,妻以为那些白发是迷失方向而跑到我头上来的异类,是偶然事件。没有想到,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我头上得到很好地印证。只用了几年的功夫,白发便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我的额头、耳根、后脑三面佯攻,迅速燎原至我的头顶,抢占了我肉身的制高点,让广袤的黑土地飘起了雪花,远远望去,就像覆盖着皑皑的白雪或是一层冰冷的白霜,令人毛骨悚然。唉!曾经让我自豪的青丝,曾经令人羡慕的青丝,就这样轻率地把阵地交给了白发。一遇到风,白发便在我头上耀武扬威,像附了静电似的四处扩张,宛若稻田的稗草在那里显摆招摇,肆无忌惮的张牙舞爪。
白发“出卖”了我的年龄。从此,我乘坐公交车,会有人主动给我让座;邻居见到我,也总是客客气气地跟我打招呼:“退休了吧?”这话是对我的安慰还是讽刺?我实在是无法洞察,感觉却是怪怪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而我还得装着轻松地回复他们:“快了,快了!”每次走进理发店,理发师也会很轻柔地对我说:“阿叔,您需不需要染发?”我尴尬地笑笑,应付他们说:“下次吧!”然后,他们会锲而不舍地劝我:“阿叔,您应该改变一下自己了!”我很默然,不知说什么好。可我心里在想:我有那么大年纪吗?
不知是哪一天,也不知是在哪一年,驻守在我生命顶峰的发丝被岁月赶尽杀绝,在我头顶形成一片“不毛之地”,露出空荡荡的头皮与日月同辉,让我顶着这颗鸭蛋四处丢人现眼。慌得我急忙把发丝养长了全部梳上去,让“地方支援中央”,把发丝集中到头顶,用几缕残发笼罩我那半秃的脑瓜,呈现出月朦胧鸟朦胧的意境,好让我整个人看上去依旧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当然,我也完全可以倾其所有,把所有的头发都梳到前面来,让“后方”支援“前线”,以保证白云压顶并垂下一帘厚厚的发丝以示体面,可如果这样,我的后脑就会骂我没脑,我得顾全大局。可忙起来,无暇顾及盘踞在我头颅之上的十万大军,只能放任自由,让他们傲立在我头上“笑春风”,这下,我又获得了一个“不修边幅”的美名。
发丝覆盖的是头皮,衣裳包裹的是,因为装饰了不同的衣裳而分出富贵与贫贱,低俗与高雅;头皮因为覆盖了不同的发型而显露出不同的追求与修养,味道与风情。成功人士的头发,盘上去是顶上的学问,泻下来是肩上的文章,即便不梳不理,也像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的作品朴素而自然,是唱给人间的情歌。我,一个下里巴人,让那么多光阴积淀到头上来渲染我的人生,总是让人感觉不伦不类,我也坦率地承认:这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失败!有时候,我的手会不由自主地触摸到我的头顶,这下可好,像是触摸到自己的无知和虚度光阴的疤痕,莫名的懊恼便会涌上心头,让我忍不住责备自己:“丢脸!”
今天,是我五十六岁的生日。妻在为我庆贺生日时,忽然提起帮我拔除白发的事,我一愣,立即孩子般地笑了,肥胖的脸颊上猛地腾起两片火烧云。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那些不可再返的时光,象疯了的野兽般冲了出来,我的眼前便迅速掠过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六岁那年,乡村理发师给我修剪的那个潮发型,让我威风了整整一个夏天;刚参加工作那阵,烫了个金黄色的卷发,带给同事们的赞叹与尖叫;参加小王婚礼,我头顶雄狮般蓬勃的厚发,照亮了整个婚宴现场……唉!俱往矣,看今朝,五十六岁的我,头发稀疏,黑白混杂,脑门光光,成了鲁迅笔下的勇士,敢于直面渐露光辉的头顶,敢于正视早生的华发,让我感叹“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白发以先斑!”
为此,我试图借助减缓白发的生长来抗拒生命的一次次落雪,赶在大雪封山之前挽留住某些悄悄远行的记忆,所以,我曾勤勉地梳理我的发丝,也曾抹各种生发膏,像农家精心耕耘他们的土地。但是,时光匆匆如流水,岁月一去不回头,发丝们没有理会我的挽留,纷纷告别对故乡的依恋,旋转着完成它们最后的精彩,随后,把一切美好的瞬间变成了曾经。看着我无比珍爱的发丝依次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与我渐行渐远,一股强烈的凄凉与无奈就会扑面而来,让我感觉那是一场场诀别,那是生命的枯竭与消逝,惹得我两眼朦胧,怎一个“惨”字了得!有时候,我会把掉在地上的脱发捡起来,让它们躺在我的掌心,枕着我那纵横交错的掌纹,让我为它们举办一场隆重地告别典礼。
呜呼,我说不出话来,以此纪念逝去的青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