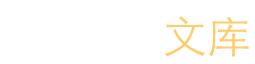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什么是世界文学?》是一本由大卫·丹穆若什 (David Damrosch)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5.00,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世界文学?》读后感(一):Had we but world enough,and time|结语的标题好在哪里?
我非常喜欢丹穆若什的这本《什么是世界文学?》,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学术性和趣味性兼备的佳作。
如果要安利给朋友比较文学相关的书籍,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推荐这本,如果朋友说他只想读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便会推荐最为精彩的结语,如果朋友说他只愿意读三段,那么我会推荐丹穆若什关于世界文学著名的三重定义,如果他说他只能读其中的一句话,就一句,不能再多了,那我会建议他读一下结语的标题——
“World Enough and Time”(“如果有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
这个标题实在取得巧妙,丹穆若什真是天才,我无法想象冠以这篇结语的无数可能标题中胜过它的存在,它含蓄而优美地表达了无比丰韵的意象——
“World enough and Time”取自Andrew Marvell的名诗《To His Coy Mistress》开头的句子“Had we but world enough, and time”,这首诗的主题和莎翁十四行诗集的前十七首类似,属于典型的劝婚诗,用来劝女子趁青春尚在之时抓紧婚嫁;那么丹穆若什在这里间接地引用这句话有什么用意吗?是因为其中出现了和世界文学息息相关的world和time吗?其实丹穆若什的用意主要在于这句诗中未出现的后半句——“This coyness,lady,were no crime.”——中文翻译过来的意思便是“小姐,你这样的羞怯便算不上罪过”;丹穆若什其实用这里的“羞怯”指代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其实牵涉到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异端、固步自封的傲慢、抱残守缺的愚蠢、坐井观天的局限、不愿阅读的无知……总的来说,原诗中小姐的羞怯和丹穆若什引句里的羞怯都是同一种“对于他者的羞怯和对于接触的拒绝”,只是在丹穆若什结语的语境中,这个他者的含义不再是追求的男子,而远为广泛。
如果这个世界无穷无尽,时间永恒不易,那么这种“羞怯”便算不上是一种罪过,但是韶华易逝,尘世易朽,“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而横陈在我们面前的是无垠的沙漠,墓穴会将一切美好的事物掩埋,歌声也将不会回荡,坟墓是个隐秘的好地方,但我想没人会在那儿拥抱”,因此“趁着青春色泽还像是朝露般在肌肤停留,趁你的灵魂自每个毛孔欣然散发出实时的火焰,此刻就让我们玩个尽兴,像是发情的猛禽般宁可把时光一口吞掉,也不要慢嚼在嘴里虚耗”,“我们虽然无法叫太阳驻足,却可使他奔跑向前”(译自《To His Coy Mistress》)。
这种经由“尘世易朽”的无奈推演为“及时行乐”的热情,在劝婚诗中非常普遍,而在丹穆若什的结语中,“尘世易朽”的无奈具体表现为“足够坏的消息就是文学作品多到没有任何人能够读完”,言外之意是百年易逝,人都是要死的,因此对于异域的他者,一切美好之物焕发出全部的热情吧!
正如本书导论所引歌德在《艺术与古典》中的话:“哪有博物学家在镜子中看到了神奇的事物,而不感到快乐的?思想和道德领域中的镜子,就是指每个人都只是自我体验,一旦他的热情被激发了,他就会明白他所获得的很多知识,正是归功于这面镜子。”丹穆若什在结语的标题中呼唤的热情正是源自相逢于异域和他者时所目见的神奇事物,这种生命力勃发的热情是歌德式的。
《什么是世界文学?》读后感(二):关于“墓地之爱”中短诗的可能解读的一个猜想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但我有一种直觉,这种解读是可能成立的,因为从这个视角出发,很多原先无法解释的暧昧之处都变得清晰了起来。
丹穆若什在“第四章 墓地之爱”中详实地分析了“纳赫特-索贝克墓地的抄写员创作的古卷中发现的情诗”中最短的一首,辛普森(W.K.Simpson)将其作了如下翻译:
然而这首诗当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疑点,即使它“没有任何缺陷,甚至没有任何不认识的词,也有正字法和语法上的难解之谜”。
丹穆若什指出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的叙述者到底是谁:“男士?女士?男士和他的朋友?仅是这位男士的朋友?这位朋友和女士?”关于这个问题,他参考了诸多版本的译文和各种假设,最终还是求助于研究者加德纳誊抄的象形文字,因为一般而言,原文应该很容易解决性别问题,因为象形文字中“我”和“我的”取决于所讨论的对象,分别用坐着的男性或坐着的女性的象形字来书写,文献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加德纳的象形文字誊抄中就可以看出:
但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更为严重,这些符号是并不一致的,第三行“it is to me embracing her”中的“me”刻写的是一位坐着的女性,下一行“my tunic”中的“my”原文是位男性作为限定词,这个矛盾该怎么解释呢?
丹穆若什认为,“不管怎样,抄写员出现了笔误”,接下来他论证了这点成立的合理性,并将论证的兴趣转移到翻译理论上来,但是这首小诗仍然引起我很大的好奇,我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出现“endures Amun”这个表述,莫非是一种古埃及情诗的传统?我对此并不了解,但我猜想其他的古埃及情诗中少会有这样的表达,因为“Amun”在这首诗当中是有着特定的意象的。
阿蒙神和儿子之间有着这样一个传说:
而阿蒙这个名字还意味着“the hidden one”,象征着隐秘者。
因此,我个人以为这里的“mss”不该翻译为“tunic”(罩衫),或是“dress”(套裙),而应该译为“bandage”(绑带),木乃伊身上缠绕的绑带。
关于原文中前后性别错乱的问题,应该从“Amun”这里出发解释,这个“to me embracing her”的“me”与“my tunic”中的“my”之所以会出现前女后男的表述,或许是因为这个对象的身份和“Amun”相似,同样是处于隐秘,不可见的状态——它可能是被绑带缠绕的木乃伊——这也完美地契合了这首短诗创作者的身份(纳赫特-索贝克墓地的抄写员),也和阿蒙神的象征(鹅与公羊)颜色相同。
当对着尸体的男子向着木乃伊表白心迹,在他的心前说话,沉浸于拥抱它的满足时,“来见你的是我”,男子作为阳世的闯入者本以为自己面前的是一具女尸,但却没想到随着木乃伊的布条逐层揭开,却发现其中所藏匿的是一具男尸,绷带搭在他的肩膀上,闯入者为他鲁莽的情欲和越界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我总感觉原诗中附带着些许幽默的意味,描述的并不全然是爱情,当然这所有的全部都只是我的猜测,我不懂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无法再做其他材料的摘引和论证。
《什么是世界文学?》读后感(三):为什么是“椭圆形折射”?
“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大卫·丹穆若什提出的概念模型,在他199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的结语中,丹穆若什提出了他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有关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其中第一个定义便涉及到“椭圆形折射”: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
这大致是什么意思呢?丹穆若什解释说:“这个折射拥有双重性质。文学作品通过被他国的文化空间所接受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源文化和主体文化提供了两个焦点,生成了这个椭圆空间,其中,任何一部作为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都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紧密联系,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的。”
看到这里或许让人感觉似懂非懂,不要急,我们不妨继续读下去。丹穆若什还解释道,他之所以提出“椭圆形折射这个意象,是打个方便的比喻,而并不是想表明这有一种科学般的精度,因为世界文学的现象乃是极其多样的”。换言之,丹穆若什借用“椭圆形折射”的光学模型并不是着眼于它科学般的精度,而是为了方便起见,想要利用这个譬喻丰富的意象来向读者阐明他的理念。
既然如此,我们便从这个譬喻的喻体“椭圆”开始说起——
我用procreate手绘了一个椭圆,A和B是它的两个焦点,有一束光从A点射出经过椭圆的折射汇入B点
第一,任何椭圆都有两个焦点。
相比于单一中心的正圆,这意味着在世界文学的目光下,单一的中心体系被打破,任何一方的民族文学都无法固步自封,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难以自绝于世,专业和领域的界限终将消弭,不同语言和文化终将得到沟通与体认,多元的价值在无数次的二元对话中呼之欲出,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与对话成为一种必然。在丹穆若什的譬喻中,这两个焦点意味着源发文化与主体文化,他者与自我,被观察的对象与观察者,它们的身份并不是绝对的,而在不同的案例中,时常可以相互转化。在椭圆中任何一个焦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丹穆若什说“任何一部作为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都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紧密联系,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其中的道理也是类似。
第二,椭圆有一条重要的光学性质,即从椭圆的一个焦点出发的任一束光线,经椭圆反射后,必定经过椭圆的另一个焦点。
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两个焦点已经确定下来,而椭圆的形状却未可得知时,可以采取的方式是在一个焦点摆上一个手电筒(也就是射线),将其旋转360度,你会发现在旋转过程中的时时刻刻,经过椭圆内壁反射的光线都会经过另一个焦点,而在椭圆内壁上产生的无数个反射点便勾勒出了椭圆的形状。知道了这个性质,我们便可以更为生动地理解丹穆若什的这句话里——“源文化和主体文化提供了两个焦点,生成了这个椭圆空间”——椭圆空间是如何生成的了。如果我们将一束束光线理解为一次次跨文化阅读和世界文学传播的喻体的话,那么正是源文化(焦点A)和主体文化(焦点B)之间一次次的协商交流与沟通影响塑造了这个椭圆空间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个椭圆空间并不是理念的构想,而更是实证的产物。
第三,椭圆上一点与两焦点相连线,一般情况下,连线的长度和越大,这个角越小,越“尖锐”(这并不是数学定理,只是一种感觉)
如下图中C1与焦点的两条连线和(C1A与C1B)小于C2与焦点的两条连线和(C2A和C2B),并且C2的角小于C1的角,也即C2比C1更加尖锐,了解这一点后,再来读丹穆若什的这句话——“文学作品即使进入了世界文学的传播中,它们身上依然承载着源于民族的标志,而这些痕迹将会越来越扩散,作品的传播离发源地越远,它所发生的折射也就变得越尖锐”——便可以发现这里是一个机智的双关,丹穆若什既在描述椭圆中的一类光学现象,又在指代世界文学传播过程中的特性,“尖锐”既是指光学折射现象的夹角,又是指文学传播中不同文化读者接受的差异。
第四,任何一个椭圆都可以围绕着一个焦点旋转,另一个焦点会落于广泛的空间内。
这句描述在数学上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废话,但是在丹穆若什的理念中却涉及到从二到多的理论推演。如果说单一文本的传播和阅读正如在一个椭圆中发生的焦点折射,那么在丹穆若什看来世界文学的空间由无数个焦点不同却又彼此相联的椭圆空间组成,这个无限叠加的过程类似于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当我们只考虑一个单一文本或一组文本时,也许我们就足以理解世界文学的椭圆状,但当我们试图看得更宽广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身陷大量的部分重叠的椭圆中,它们共享主方文化(host culture)中的一个焦点,但它们的第二个焦点却在时间和空间里分布得更加广泛。”——如果要用图解的方式来想象这个无限的过程,大概是像下图这样的。
画得有点烂,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旋转的过程无限重复,并填满整个空间,这就是丹穆若什提到的“时空中更为宽广的分布”
第五,折射的过程并不是“椭圆”这个意象的全部。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看过阳光下斑斓闪烁的椭圆形宝石,那是太阳光穿过其中经过复杂折射反射的产物,这种缤纷闪烁的璀璨图景便是世界文学的异域情调和多异之美,一道光在椭圆中的折射或许并看不出来什么,但是无数次折射的过程便会呈现出一道道溢彩缤纷的光虹,这是在丹穆若什看来世界文学的殊胜之处。
对此,丹穆若什也有进一步的生动描述:“在迪士尼乐园晚上九点左右发生的一个景象,我认为也许可以更好地形容这个椭圆状过程。当人群沿着美国河流的湖岸线聚集起来,期望去找寻一些比美国小镇大街中的机器人幻影更有魔幻魅力的东西时,街道上的灯光暗下来,音乐声增强,接着一片水从隐藏在汤姆索亚岛上的沙滩中的一团密集的喷嘴中喷射出来。在河对岸,一束束强光越过河流,在弥漫着雾气的大屏幕上汇合,屏幕上投射着动态影像:米老鼠、魔法师的学徒,介绍着晚间的娱乐表演,形成了一幕由投射灯光和折射光线的水面结合而成的波光粼粼的景象。”
最后,我想再说关于“椭圆形折射”这个譬喻来源的一个猜测,它应该是来自于开头导论中记载的歌德的一席话:“每个民族文学如果局限于自身,而不通过外国文学的滋养而得以更新,它自身的活力就将枯竭。哪有博物学家在镜子中看到了神奇的事物,而不感到快乐的?思想和道德领域中的镜子,就是指每个人都只是自我体验,一旦他的热情被激发了,他就会明白他所获得的很多知识,正是归功于这面镜子。”
歌德所设想的“思想和道德领域中的镜子”经过无限的拼接,形成彼此相连的一千零一面,弥合为椭圆的形状,倒映着彼此的容颜,“我”从“你”开始,到“你”结束。
上一篇:创造力觉醒读后感锦集
下一篇:暮色读后感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