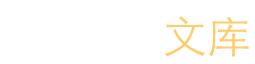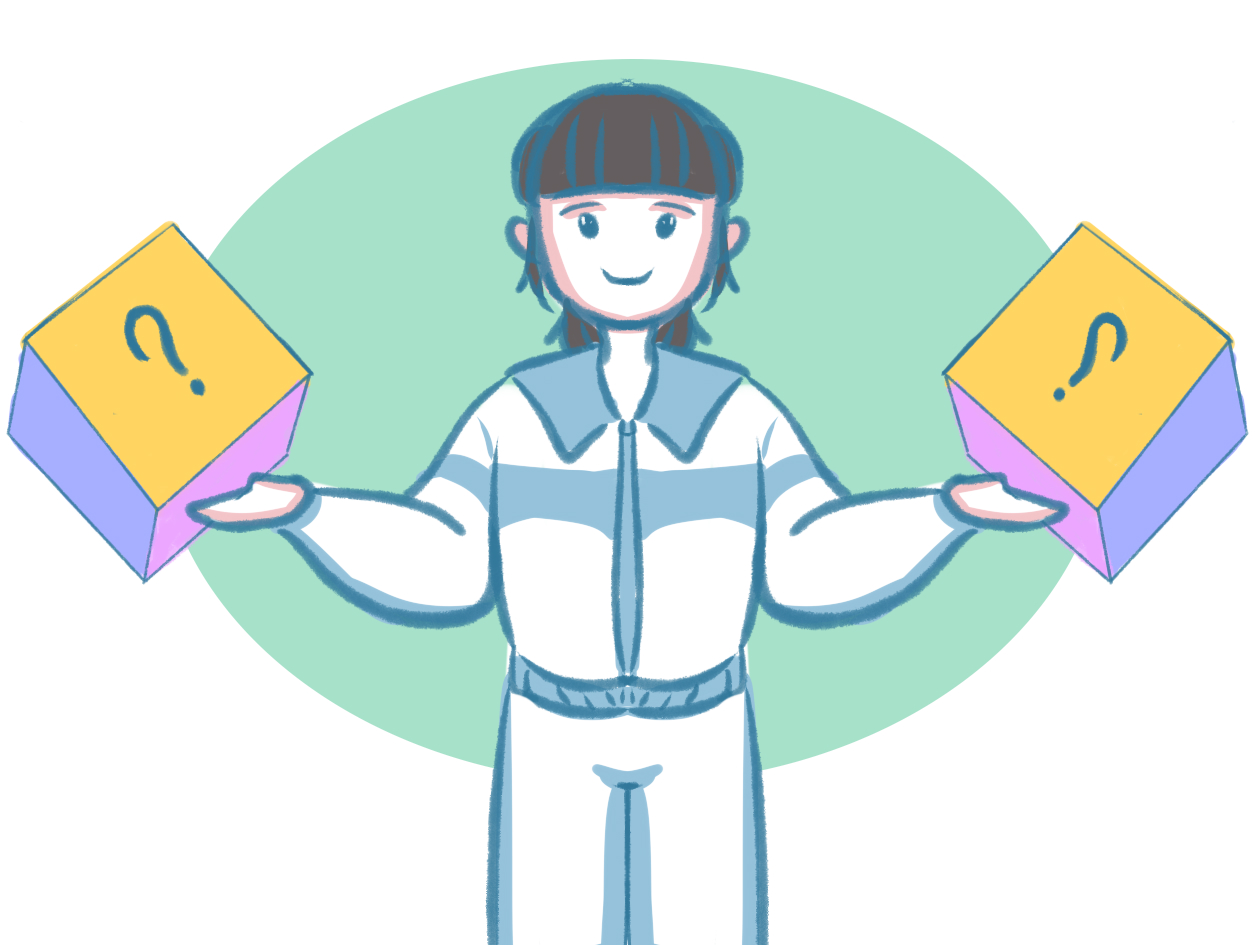“冥昭瞢暗,谁能极之?”。正如远古人类神话中浑沌地认为,天地的起源是浑沌的,没人弄得清楚一样,我对于我的祖先、先辈们的认知,甚至对社会的认知也是“浑沌”的。
金属冷兵器之前,靠徒手棍棒打天下,其家族氏族的繁衍联系至关重要,虽秦皇汉武也唯留塚茔,但商周后金属冷兵器几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仍显家族的兴衰之重。近现代家族氏族势力渐淡,可民族国家的人口仍是强大的根基之一,人类社会总要有些形式的群体联系,家和宗亲仍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细胞和细胞团。
年轻时的我很淡然家族观念,也许人一老返祖现象会多一点,因就有时会想起一些过往。一个家族在当地繁衍数百年,枝枝蔓蔓应该是庞大的,不管里面发生过多少大小故事。而我却对我的祖辈、先辈知之甚少。即使最近端午节放假,我驱车一百多公里,从市到县到霍河库区的尾岸边,和我小姐一起拜见了尚在世的我唯一的长辈、时隔四五十年未曾谋面的“小叔娃子”,仍是浑沌一片。
还是在我小学初中的时候,“小叔娃子”一年里能来县城我家三两次。儿时记得“小叔娃子”,眼睛总是不太好,红红的老眨巴眨巴,有时甚至眼角还有粘连物。不象是视力问题,而象是农村常烟熏火燎的眼。此次去,眼仍是不太好,但干净。“小叔娃子”来家时,大多担着一根被汗渍浸润的很油亮的酱红色桑木扁担,扁担上一头常绑着空口袋或棕绳子,是送我家东西还是到城里卖东西或是挣挑货钱,不知。
“小叔娃子”,叫什么名字?因短暂的一天,我没顾上问,也不好意思开口问。但“排行”肯定和我父亲一样,为“继”字派。“小叔娃子”说他属羊,今年七十二岁,看样子,身板还算硬朗。听说,闲不住还天天到山坡上的地里干活,那可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闲情逸致,而是辛勤农耕一辈子啊。还没进门,就听陪同的小堂妹咕叨说:“前几天,自家的牛吃了别人家的红薯秧子,人家要赔五百块钱。就是秋里把那块地里红薯全挖出来卖,也卖不到五百块撒,哪儿有这样的邻居村民?”,可我“小叔娃子”喃喃诺诺地说:“人家是寡妇,人家是寡妇,拖儿带母的造孽”。
我小姐大我三岁,疑“小叔娃子”耳背,见面后便大声问:“小叔娃子,我是谁,还认得我吗?”,令人失望地是“小叔娃子”摇了摇头,答:“不记得了”。我和我小姐可不能象小品相声中那样让“你猜啊,再猜”,给自己找尴尬。小姐有点沮丧,便自报了名字。我也大声说:“我叫竹茅子,您那时去我家时,我又瘦又矮不大说话”。旋即,“小叔娃子”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终于唤醒了我长辈对我的记忆。
其实“小叔娃子”只比我大十四岁,在我小时候,他不也就是二十多岁?比我大哥大姐都还要小。也是因此吧,大人教我喊“小叔娃子”。我大哥七十多岁过世已十多年了,大姐尚在但也已七十七啦,身体似乎很飘摇。
“小叔娃子”后来说:你们的爷爷是仨兄弟从江西过来的。我有些不信,江西姓“竹”的少啊,而北方省份多。但姑的儿、姨的儿,我从小就叫他们“佬表”。姑不叫姑,叫“娘儿”,也有喊“大”的,而“姑父姨夫”还是这样称呼的。长辈,不姓竹的,就称“表叔表爷”或“干佬儿干妈”。这是否江西某地域人际的称谓,不得而知。但我晓得,在我老家那县姓“竹”的少之又少。还有一传说,山西洪洞在前朝几百年间强行移民时,后人都有其特征:上厕所叫“解手”,“解大手解小手”;小脚指头指甲外侧裂一小瓣;走路背起双手。在我们小城很多人都符合这个特征,我亦如此,难不成“祖上”是北方移来的吗?
爷仨,大爷叫什么?不知。“小叔娃子”说:“他有一儿叫“继武”,解放前那会儿听说跑台湾去了,死活不知,你爷是二爷”。二爷叫竹什么?也不知。我奶奶姓何,我知。我朦胧的记得,蹒跚学步的时候拉过我抱过我。幺爷叫什么?这次没问还是不知。幺爷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是眼前被我称呼的“小叔娃子”。大叔娃子已过世,这天大叔娃子的儿子指给我,河叉弯那边,埋在水库淹没线上的一块靠山根的平地上,那棺坟便是。说推脱地话,时间短,我这次也没顾得去祭拜一下烧些纸钱。这要搁河南、东北人的晚辈是万万不会的。湖北人,确切地说汉江“朝秦暮楚”地域出生,又“多元”文化熏陶的我,看的淡一些。正像武当山周边地域的原住民,三跪九叩到金顶的人并没有,虔诚进香的都是外地人。本地人即使匆匆而去,也只是为头疼脑热、遭灾遇难后、逢人生十字路口的烧个香,祈求后来的日子避凶化吉顺利光明些,心理上能解决点儿“实际问题”。而我连“香”都不愿烧,年轻时从事人事工作陪退休老干部、中年时当单位负责人陪北京来的客人、老年时退休后陪着外地战友三上武当山,没烧过香。曾经去过杭州的灵隐寺我也没烧过。到那幽幽冥冥的历史肃穆之处,我总是静静地看,静静地浮想联翩。在别人眼里,我是否有点儿“另类”?
午饭在“小叔娃子”家,堂弟听从市里赶回来的小堂妹说我们要来,责怪她:“哥他们要来你昨天不说,要不那条蛇就不卖了”。话里可见堂弟的血缘真情,未曾见面,堂弟又到山坡上逮蛇去了。蛇好像是保护动物,并且被蛇咬着咋办?我不大希望他们去逮蛇,但又有点盛情难却,好在也没逮到。
仿仿佛佛地记起,听大人们说:六七十年代幺爷他们家贫,农村里就指望土里刨点吃的,过得艰难不说,屋漏偏逢连阴雨,那老屋还失火两次烧个精光。现在好了,幺爷虽去世,但大叔娃儿和小叔娃儿两家都从偏远山上搬到了山下的水库边,盖上了二层楼房。午餐桌上特别风味的就是库区捕捞的鲜鱼,那味儿是咂的出而道不出的。
想着不便,午饭后我意欲赶回县城住,“小叔娃子”挚热低语的说:“歇一夜吧歇一夜吧”。大叔娃子的儿子,我另一大堂弟也再三挽留到他家吃顿晚饭,大堂弟媳也真诚地说:“从这儿走下去到我家没得好远,去尝尝我的手艺吧”。午间吃饭时便觉得这个大堂弟媳挺能干的,而大堂弟亦是“竹”姓遗传的性格:耿直不愿求人,说话不怕你受不了。两个叔的两个儿子家,吃一家不吃一家的,似乎有点儿不妥,于是便答应晚餐在大堂弟家。走在乡间小路上,大堂弟话间,突然冒出一句:“小姐在当行长,她还来过我们这儿,我们也去过她们行。你那时当行长,没敢去,要找你,还懒得理我们撒”。我装没听见默不作声,是的,我小姐那时在中行了,在亲戚中善帮忙,比我大方热情些,有亲和力有威信。那时我咋就没想过联系联系他们。心想:这大堂弟似乎没见过面,也不记得他找过我办没办过什么事,那时是否有找过我贷款又回绝过的事?要说正派,我那时倒还称的上,现在回首往事,心怀坦荡。不过,有些事在亲情上没“照顾”到,现在心里总会有一丝愧意。但凭心而论,一生没作过恶和做亏心事。也就没有在良心不安时需要揪心地忏悔的,更没有需要像《十日谈》故事中的“夏泼莱托”,无恶不作后编出“道德美丽”的忏悔。
九十年代后当了十多年支行行长,对家门中的同辈晚辈我都没额外地关照帮助,也没有贪念谋些私利,总怕别人戳脊梁,背后飘来鄙夷的眼光。安排了多少职工子女和复退军人,就没有“开后门”安排自家的亲戚。“竹”姓的人大都嘴直心善,母亲常挂嘴上的一句话:“要想俩好,打个颠倒”,让我“当干部要有干部的样儿,做事不要让人戳脊梁骨”。像五六七十年代常嘱咐我那在供销社的大哥一样,嘱咐我“不要贪占公家便宜”。想着“正气”,便释然了大堂弟那句让人不痛不痒的话。
晚餐自然是贤良的大堂弟媳操办,真真的土鸡和水库里渔网上刚摘下还甩着尾巴的鲜鱼。用那自家菜园子里才挖的洋芋炖的母鸡汤亮黄鲜香、自家山上扳的竹笋晒的干儿炒自家腌的红腥腥的腊肉……。无需广告中的“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有机富硒”之类诸如的词汇,看一眼便有些垂涎欲滴了。
大堂弟还是有“竹家”男人的家风,自不必交待老婆饭后收拾家务琐事,操起门前坎下他泊着的机动渔船,载着我、载着小堂妹夫和五岁的小堂侄,在旖旎的库区或快或慢尽情地开去。山间蜿蜒激荡奔流的“地表水”,不管它是溪是河是江,只要找个口子筑个坝把它一锁,它就会平静下来,变得宽厚宏大,让山变矮让山变岛让山投入她的怀抱。大堂弟像玩儿似的操着船,在这端午节稍热的季节,宽阔的水面晚风拂面,感觉是这么清爽和惬意。遇着沾满希望的渔网,他会熄火压下柴油发动机,让旋转的浆叶停下来抬出水面,使船儿轻轻地拂过渔网拂过水面,而后开足马力向着夕阳奔去。船头分开碧水,荡漾的水波向后向两边八字的播散开去。不禁让人联想着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不也激起了看不见的引力波向宇宙四散开去?船尾在螺旋桨的搅动下,抛起一溜充满欢快气泡的银白色浪花儿。夕阳斜射在碧水上,闪耀出片片粉红金色的鳞光。我此时只有“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的轻松心境,断没有诗人“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的感叹。毕竟现代是公平的成熟的商品经济,不似往年历史下的社会经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虽两三千年了,但赋予它内涵意义的社会制度、政治生态、商品交换环境不同。现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靠水吃水”的人们不再是风里浪里十分艰辛地为糊口在剥削压榨不等价的交易下打渔了。
建这个装机一万千瓦的土石坝电站水库,还是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那两三年间。土石坝高七十余米,库容一万万方,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只有人力推车、钢钎、大锤、少量的炸药。那时我正在部队服役,搞得是三线建设国防战备工程,其施工先进程度不能同日而语。一九七七年我在部队就开上了新接装的ZL450装载机在山洞里施工,那一铲子下去就是三立方啊。建这个水库电站,依稀听说,全县动员几万“大军”,各公社建“营”,各大队建“连”,县城各部门派员“参战”,拉一手推车土石发一毛钱的票,农民拿票回去换工分,集体部门拿票去县里换钱。此一时彼一时,搁现在不可想象。这个电站的建成,是县城继一九六五年拥有第一台五百千瓦柴油发电机组后,又一电力发展的里程碑。
我爷兄弟仨,推算起来应是清末来到竹山。为什么来?怎样来?其有无悲欢离合的故事,逃难逃战?已无从考证。“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们背井离乡到这偏僻之地,其苦其志可见一斑。
我的爷爷,也就是仨兄弟的老二。在我出生前啥时候就没啦,奶奶在我四岁时过的世,咋想也想不起她模样,只留存有一丝冬日里拉着我到下边的农具厂外的老城墙台子上晒过太阳的缥缈印记。二十多年后,我大哥在老坟场“灯盏窝儿”(注:地名,当时小城葬人之地)坍塌的一堆石块里,发现一块仅刻有诞辰、卒年、姓氏的破败大青砖墓碑:竹何氏。
父亲去世时,我才六岁,少不更事。停丧入殓时,我还围着棺材玩儿,看着大人们在父亲遗体头边塞放着皮纸包裹的硝灰包,全然不知大人们的悲痛,也全然不知我少了什么。跟着举着阴幽之气白色的“清明吊儿”、撒着纸钱送殡的亲朋街邻,蹦蹦跳跳走了六七里路,随着娓哀的锣鼓喇叭声到“灯盏窝儿”,直到下葬入土后,我的胖头油面麻子篾匠幺姑父才叽里呱啦地让我跪下磕头。而后,“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大地、荡涤精神。那一片曾经入夜冥火飘忽、寂静无籁,白昼又时常哀乐响起、鞭炮噼啪的坟园,渐渐地寂静了,渐渐地垮塌了。垒坟的石块成了梯地的石梗,培坟的黄土种上了庄稼蔬菜。人们忌讳了淡忘了忘却了,在清明、在大寒、在除夕去扫墓祭拜先人。往往在这些时点里,只是在心中嘴上念叨逝去的先人们的轶事、恩情和让人咂嘴称道的为人品格,就连在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活埋的共产党员新四军干部,民主政府县长许明清烈士墓地也悄无声息。
八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去世时,已五十岁的大哥又在坟扒(地方音:pa,义:园地场地)里寓寓沉默地转着,在菜园子的石摞中终又发现了刻有父亲“竹继志”名字的大青砖墓碑,象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捡起来抱着,砌进了母亲的坟窑儿里。那时,我已退役在银行上班,渐渐懂些事了,知道大哥作为长子的艰辛,一手操办了奶奶、父亲、母亲的丧事。
改革开放之初,打破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禁锢,让人们思想活跃起来,进而解放了生产力。但流传了几千年,是否“糟粕”的东西也随之泛起。当弄神信鬼之风越演越烈之时,婚丧嫁娶、搬家动土,甚至于办公桌的朝向这些“风水”都大讲其究。把人与天地宇宙气场引力波关联起来,美其名曰:这是人类还没法解释的“科学”。[英]天文学教授约翰。保罗说:“完整无缺的认知实在是悬在天上的一块诱人馅饼。这是各种伪科学的特有标记。迄今为止,那些用错误的观点来解释我们世界的理论仍带有这样的标记。占星术企图得到一个将星的方位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的确定关系。”我有时会“孤陋寡闻”地静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不灭,物质守恒。人的生死组成,就连活着的生命、大脑的神经元,若把它彻底地微分化不过是分子、原子、粒子、量子循环的组合变化罢了,或者变成“反物质”了,反物质在和物质循环?人类或者个体的人在宇宙中仅仅是过客,宇宙的变化能决定人类及其生物的诞生与毁灭,并不决定个体人的“前途命运”。
我们不要把未知的东西去“胡编”它,去“神化”它,人们可以张开想象的翅膀,想出美好、想出进步,想出科学前进的先导,凝聚起人类的高尚精神,而不能想象出一根绳索来束缚我们自己。
在我离开银行多年,去“自由职业”时,曾在路过湖南张家界的列车上,遇一同座位的她。初始,看着青皮的光头,我以为是男的,当说话细看吓人一跳,打量是三十出头的女性。她虔诚地递过一本印刷劣质的小册子,扫一眼那“十字架”,知是基督教之类的。她侃侃而谈说:上帝创造了人类……;我问:上帝是指宇宙吗?她说:不是。我问:上帝是干什么的?她说:上帝嘛就是上帝,上帝是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我问:救世主耶稣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吗?她答:不清楚。我说:要说人类是宇宙创造的,我信。要说上帝不是宇宙而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信仰的至高“神”,并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我不信。马太福音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可我的理解是,人类是适应自然进化而来,不是上帝创造的。恰恰相反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让“他们”无所不能。没有了人类或人类没有出现过,宇宙照常在,也不会有什么“上帝和众神”。外国的宙斯、普罗米斯修也罢,耶和华造耶稣造亚当夏娃也罢,中国的玉皇大帝也罢,都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无知和人类精神的需要想象杜撰安排又为人类或者说权势阶层服务的。巴黎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在国际歌中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上帝,圣皇和晴官;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也许她见我不是可“教化”之人,也就一路无语了。
在市区银行那会儿,“法轮功”正是蛊惑人心高潮之时,行里也有几个似乎在“修炼”的,我在职工会上“告诫”:“你信你练,一是不能到街上练,影响交通影响他人影响社会;二是你在家炼,不能影响家人正常的生活,至于你不吃饭不吃药,省钱啊,行里少开支些医药费。真正的“神”、真正的“功”应该是有利大众的”。没收了几本“法轮功”书,翻了一遍,说的天花乱坠神乎其神,文字语言不成“文章”,稍有文化稍有理智的人就会嗤之以鼻,“胡说八道”嘛。会后,行里那几个人也就没在炼了。二十几年退休后再见面,我会感到他们那时可笑的愚昧,现如今和其他退休之常人一样生活,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养老和医保,安度着晚年。不过,社会生活,难免不遇身边讲究“玄学”之人,争之,他总会说我:你不懂。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个体人的纷杂思想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我仅是相信,人的意念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肉体凡胎。
说来也怪,父亲如何死的,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觉得与我有关。父亲那辈,推论起来也是兄弟仨,大伯幺叔我都没见过,其姐妹,我的三个“娘儿”倒是在高中前的年月有过往来。
六十年代我见过改嫁后的大妈,我大伯叫什么?不知。可能解放初病逝,无后。在我一九七六年底当兵政审的材料中,居委会主任苟大妈是这样写的:“解放前夕当过国民党伪保长,比较和善,没有民愤”。这是我以后有权能看到我自己档案时看到的,没有刻意记住我大伯的名字,也没有留意政审中其它的细节描述。那时“材料”中,如要写的是“有点民愤”,我或许就当不成兵啦,以至于改写我后来的命运。
改嫁后的大妈住在八里路远外城西的小漩儿(地名),后大伯会些篾匠手艺。房子是黑灰色石片瓦盖顶的木架房,房前是一条小街,土砂石的公路上车少,行人也稀少。房后是菜园,周围隔墙用河里卵石块摞着有半人高,菜园外边是砾石沙滩和一丈多高或青或黄的芦苇,再下就是堵河啦。说是涨大水时,水能漫进屋子。大概七十年代啥时候,大妈和后大伯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堂姐,因传这里要建水电站,以移民搬迁理由一起回后大伯老家河南南阳了。没想到,几十年后,这里连成了小城扩展的新区。
那时,小学放暑假了,我有时和小姐,有时和幺姨的比我大一岁的独儿佬表,到母亲的老家曾武沟乡下舅舅的家,路过大妈家也要去玩玩。从城里沿着土石砂籽公路走一半路时,左边几十米下是湍急的堵河,右边是陡峭的大山。因为小,走不动路,走到这地方便会歇歇。那里,山岩石坡上长着浓郁的枞树,在一人多高树荫掩映的地方有一很小很细的泉眼,泉眼口儿有一小水坑儿,水不过几升,周围长满了青苔,顺手摘下一片光亮的桐子树叶,围着叶蒂把儿一卷,就成了圆锥形杯子,舀水时虽漏水,但不碍喝水,那水真凉清甜、沁人肺腑。回想起来,那真是“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的意境。似乎高中以后就没再去大妈家,从此渺无音讯。至于到舅舅家,压根就没“wei(注:地方音)爷、婆婆”的概念。竹山把外公叫“wei爷”,也没人究其读音意思,只是传承着固有的口音叫法。后来,我分析wei爷就是“外爷”变异的读音,就是外公的意思。现在,我很爱我的一两岁的外孙儿外孙女儿,可我却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外婆。人说;“老小老小”,就是说人老了有时的举动思维、生存能力反而会像孩子一样,我便想象着十分羡慕享受过外公外婆爱戴的外孙儿们。
幺娘儿住我家街对面的后院里,两孩子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五、六岁时最后的印象,躺在床上,因我见过高高的亮亮的鼓着的肚子,尽管姑父有点篾匠手艺挣得点儿钱,也没多的钱医治,她可能得的是肝病肝腹水病死的?多年后还听我小姐说,那时还怀有身孕,就更让人默然。整个县城就两三家私人药铺,药铺的主人往往是中医世家。看不看病的街坊邻居都称中医叫“先儿”,如五六十年代小城里知名的贺家,我们去抓药时都随大人尊敬地喊“贺先儿”。直到一九六四年县城才建起一座有几栋平房的“竹山县人民医院”,因是我大姐当时所在的县城唯一的建筑大队所建,大姐带我去她干活儿的工地玩儿过,所以还有些记忆。
我父亲应该还有个兄弟,可能死的太早,因为我儿时常到下街头新街口住的舅爷舅奶家玩儿,舅爷舅奶家有个孙儿,我喊“哥”,还有街上头我不大去的一个已成家的“姐”,他俩是亲的。那时并不知“舅爷舅奶”为何亲,大了才知是奶奶的弟。可能奶奶的这个弟无后,就将我那个“幺叔”的一男一女过继给舅爷当了孙子孙女。小时,也常到舅爷家去玩儿,屋里那家具摆设现在回想,还是挺讲究的。有瓷瓶瓷罐瓷碗磁盘、木雕的花架神龛,油漆的衣柜箱子,架子床踏脚板。据说何家在小城是大户、而我奶奶舅爷是否何家旁枝,已无意考证。说实话,我真不知那些年代一些人家咋生存的,那时也有“五保户”,政府提供一点生活费,他们是不是呢?我估计不是,因为我那个“堂哥”已成人,他们不算孤寡老人。舅爷他们秋冬在街口摆一个烤红薯的炉子,倘若我上学要拐几步路从下头新街儿过东门街到北门坡去上学,走过他们炉子边,就会给我拿一个烤的热楼楼(地方音:loulou)的红薯。还有一次我不知手咋卡进了他们堂屋的木花架中的小隔子里,拔不出来急的直哭,舅奶温慈地用“洋皂”沾水打在我小手上,捏捏按按,才拔溜出来。
我那幺叔及婶我都没见过,至少在我记事前已去世。舅爷舅奶过世后,这个哥常来我家,那时我家生活虽也拮据,母亲撑着竹家门户,还是极力照顾。后来他六九年下放插队农村,为能照顾他,我大哥还把他从两百里外的乡下迁到他工作的乡下。每每从农村回城,我这个哥晚上就会和我睡在一张床上。读初高中的我,也听不太懂他天南海北的“哇啦”,什么苏修“勃涅日列夫”,什么美苏争霸,什么“洲际导弹”,什么“苏联陈兵百万”,我们一级战备“也有核武器”诸如的话题。“珍宝岛战斗”我知道,课文里有,学校也有防核防化的常识挂图,还有苏联坦克的剖面图和手持火箭筒爬冰卧雪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幅画。但睡在床上,望着黑暗的屋顶棚,还是有些兴奋惊奇。舅爷舅奶去世后,哥下乡十多年才回城在航运公司上个班。“文革”多年后,他家的“瓷器木器房产”呢?
初高中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和我小姐到大娘儿、小娘儿家去。大娘儿小娘儿都是“小脚女人”,不像我妈“大脚片子”,不过我母亲的三个姐也是“小脚女人”。据说,我妈学包裹脚时嫌疼,也许我外公外婆不在世了没人管教,后来十五岁时,经我城里住的小姨介绍,嫁给了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没敢再让包裹脚了。大娘儿在房县清峪河边住,很远,得走上一天山坡河沟路,去了一两次就再没跑了。她个子高高地,说话钢钢利落,好像很有主见的样子。来我家,常叼根烟袋,听说大儿在县公安,后来小儿得的有“羊羔疯”病,总怕他突发病栽到河沟里,所以好多年至死,大娘儿也没再来我家了。
小娘儿在田家坝花栗苦桃河边住,离城约十几公里,因为近一些,走半天就能到,就去得多一点。小娘儿比大娘儿矮的多,但看起来很“嘹亮”(地方音“liao liang”,义:能干贤惠),虽“小脚”,但精神。走起路来铿锵有力,常含笑容,眼力好且是人们常褒描的丹凤眼,有一手好针线。小娘儿的丈夫,我的小姑父没见过。听说五十年代末是个大队会计,但因被冤贪污抓起来关到了县里。那时小娘为洗清姑父冤枉,摸着风闻的线索,打听到附近小偷家中,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窃贼退了所盗钱款,把我姑父“领”出来。可我那姑父性情刚烈心胸又有些狭窄,忍不了冤屈,嫌丢人现眼,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投河自尽。小娘儿的小儿子和我同岁,我喊佬表,小名叫狗娃子。几岁十几岁我们见面,总还看见他戴着一个银子项圈,憨憨的样子很是可爱。
若小娘儿从城里带我们去她家,我会高兴地下南门坎,上渡船过南门河,翻蔡家岭,走文家边,下赶集沟,过深河。深河其实不深也不宽,只是小河的名字。在河上有一小木船,没人招呼,船头的绳子系在横跨河两边的铁丝上,谁过河谁就上船扯着挂在铁丝上的绳子,船就缓缓地几下就到了对岸。从南坝再乘大一些的渡船过堵河,到北坝。北坝可是有名的地方,因为交通不便,竹山南部山区一百多公里,人们出山要么翻山越岭地脚走,要么坐船。过去有个夸张的民谣:“官渡府峪口县,田家坝是金龙宝殿,无事不到外国转”,可见大山里的人要出山到外面之艰难。后来的后来,田家坝镇更名为“上庸镇”。(注:官渡是堵河上游的一个镇子,离城约七八十公里路。峪口是官渡与田家坝中间的一个码头集。田家坝即指北坝。“外国”指县城。)。
从北坝再到小娘儿家的路上,看过麦苗青青菜花儿黄,小紫蝴蝶黄蝴蝶似的蚕豆花儿豌豆花儿,金黄沉甸甸的稻穗,绿油油的红薯叶蔓下一垄垄土中露头的红皮红薯,还有一片片吐着淡黄油润包谷胡子的包谷地。苦桃河盘来湾去,浅水处河里摆放着大小不一的石头作墩,清水悄无声息地绕着石头流去,我会蹦跳着踩着石头跑过去;水深处,则是用藤条将三根碗口粗的松树并排着绑扎起来,架在水浅处的石头上或岸上的沙石上作为小桥,这时小娘就会拉着我小心地踩着晃悠悠的松树过河。
小娘儿似乎谁都认识,到处都是歇脚喝水的人家,小娘儿的为人可见一斑。那时,城里户口的人,吃粮要计划,每到月底二十五号左右计划就没啦,母亲总是会东挪西补地借啊、吃稀点啊、买点红薯南瓜啊度过月尾。我和小姐在寒暑假到农村去,或许还有能少吃点口粮,回来时还能带点儿瓜菜的意思吧。
说起吃穿,我的记忆中从没感觉小时候“苦”。粮食局供应的粗粮有包谷岑、豌豆面、蚕豆瓣儿、红薯干,细粮占比少,有大米面粉。冬日里,常端着碗在“衙门口”晒着太阳,顺嘴呼噜呼噜地喝着稀饭。除了自家腌的白菜萝卜叶儿酸菜,有时再就是一大碗酱豆汤当菜。肉,每月每人半斤计划,要到食品公司排队买,有时候有计划也没肉。割肉的时候总希望它肥些,好炼点油,其实人都缺吃的,猪又能肥到哪里去呢?有的时候就是腌的有哈喇味黄不唧溜的干腊肉。哪像现在素菜吃的要精致,荤菜吃的不敢再吃,惆怅着“减肥”。而新衣自是在过年前凭布票扯布要做的。人们生活苦不苦,幸福与否都是自我感觉自我认识,什么叫“知足常乐”?
小娘儿的大女儿,我的大表姐叫“家秀”。六十年代初,嫁给了苦桃河对岸的肖姓人家在外当兵,后转业到襄樊(注:现更名为襄阳)公安的表哥,表哥其实也是我嫂子的亲哥哥。我嫂子嫁给我大哥是否也是小娘儿牵的线或是默许,我看很有可能。
在我六岁的时候,表哥来过我家一趟。高高地个子,戴着嵌有公安警徽的红线镶边的白色大沿帽,着一身雪白的警服,腰间系着的皮带上挂着酱色牛皮枪套扣着的手枪,脚上穿一双锃亮的三节头黑皮鞋,煞是英武。我摸过那乌黑的手枪,以至于我日后拌黄泥巴做的小手枪,晒干后刷上墨汁,比其他小伙伴儿做的假枪看着要漂亮逼真。表哥带我上县城唯一一家照相馆,也就是照相师傅的家里堂屋,给我拨弄几下头发,上衣兜里插支钢笔。在大木三脚架上支着大箱子似的照相机后,照相师傅右手捏着个手雷似的小橡胶气球,说声准备一、二、就一头扎进外紫红内黑的金丝绒布里,不像现在喊“一二三瘸子”,只喊“三”,咔的一声,我便有了我平生第一张照片。那黑黑的头发尖盖在两眉梢中间、清秀的五官显出一脸的稚气、带两个光点的黑眼仁透着股灵劲儿、黑色的学生装的衣领内一圈白色的衬衣领显得干净精神。后来拿出来看,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是我的儿时。碰住妻子和女儿瞧见,都会会心地揶揄说我,“太自恋太自恋”!
那次也许是表哥回老家探亲吧,“在河之洲”行走的表哥,能不让隔河相居的“窈窕淑女”,我的十八九的姑表姐动心吗?我六七岁的时候,表姐来城里我家,要坐船到襄樊找我表哥。现在看来,那时没有“父母诸兄人言畏”,而是独赴“仲子”结连里。
推论是春夏之交的季节。一早,天飘着蒙蒙的细雨,表姐穿着蓝底碎白花的上衣,短披发,lian mao ye er(地方音:连毛叶儿,义:刘海儿)下,有双亮晶晶的眼睛。她打着黄竹把红色面儿的油纸伞,左手弯儿挎着一个深色的布包袱,没人送行,似乎也没有泪眼婆娑。只有小儿的我跟在她后面,从家出来经新街儿、东门街、到东门河,踏着湿漉漉的沙滩,表姐要上船了,回过头,摸了摸我沾有露水儿的头发。看着表姐踩上晃悠悠的木跳板,走上船头,又回眸看我,招了招手,收起雨伞,躬身进了船舱内。船夫抽跳板,提铁锚链,“咣”的一声扔下铁锚勾住船头沿,静卧船头。再提起竹篙往岸边沙滩使劲一扎,两脚紧蹬着锚后的船头,船便缓缓地离岸掉头,向下游越划越快,渐渐地木船在水天一色的河上雾中变成一个小黑点小灰点,消失在远方。
雨肯定是霏霏细雨,因为我没有带“斗笠”。县城用伞的人户极少,家家下雨出门多是用双层篾编竹网、夹着耐水的什么植物的干叶子,中间凸起一小包用头顶的“斗笠”。那时,我太小,全然不知表姐此时此刻的心境,表姐也不会和黄口小儿的我交流什么。但这一幕,我从此就再也忘不掉霏霏细雨白雾蒙蒙中,打着红油纸伞站在船头的表姐。其实“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的蕴涵,从先秦《诗经》到唐人《竹枝词》的民歌风千百年来一直浸润着秦巴汉水流域的少男少女的情怀。
如果,我那时大些懂事些,是否也会生出戴望舒的诗意:
“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那以后以及随后“文革”的到来,表哥表姐一二十年再也没有回老家了。表哥家是富农成份,表哥是人民警察,应该要淡化家庭关系,甚至是划清界限的。及至后来表哥表姐一双儿女的幼时,都是寄养在我小娘儿家,就是寄点钱贴补父母亲也是通过我小娘儿悄悄地转交,尽管爷爷奶奶就住在小河对面。表哥的父母,也是我嫂子的父母,我喊干佬儿干妈。记得在一个寒假,到小娘家玩儿,也曾到他们家住过一夜,才睡时,身子下的竹席子冰凉,盖的厚被子又压的人喘不过气来。睡过一会儿,席子暖热了,整个身子才暖和和的。其实,干佬是勤劳的,从早到晚总是看他在地里家里忙忙碌碌的。
九十年代,我那“窈窕淑女”的表姐,把我小娘一家老少从穷乡僻壤的大山之地都迁到了她所在江汉平原城市富庶的郊区,也算尽了孝心,对弟妹们也算尽了责任。但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小娘八十多临终前,大表哥慌慌地给表姐打电话说,这回病重的很。表姐座机那头吱啦吱啦响也没听清,以为过世了,就急匆匆地买了些花圈带着子女到郊区小娘住家门外,噼里啪啦地放起了鞭炮。大表哥相当地尴尬,小娘在病榻上听得是给她放炮送花圈,一气不两天,真的临终了。这些事等,都是后来我小姐告诉我的。
说到竹家,女性多是勤劳俭朴能干泼辣,虽未必知书但却达理。而男人们外表多有些懦弱,内心却掩藏着些许暴烈,间或会迸发些想入非非的念头,说直白点,成不了大器。
父亲有一张遗照,可能是五十年代在城关镇食堂做饭填的什么登记表上揭下来的,泛黄的一吋照片右下角压的钢印已看不清什么单位字。圆圆的脸庞,看起来,憨厚老实。我小姐听我母亲数落他说:解放前那时,家境困难,让他去四川挑盐卖,盐不是被山匪抢了,就是路上绊跤滑倒散落了。大娘儿给点香油吧,他能在路上把装油的竹筒摔破,油漏个精光。但父亲炕的一手好饼子,最后还是到镇食堂做饭去了。父亲有吼喘病,正规说法是哮喘,一到冬季哮喘的就特别厉害,咳的人腰佝偻起来,出不过气。当然这时已没在镇上做饭了。
我渐渐地长大,却莫名其妙地迸发出怪异的幻觉,脑子常闪现一个影像:一个黄昏后的晚上,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咳着,床头条桌木箱子边,一盏昏暗的桐油灯,就是像炒菜锅的形状,不过很小,只有巴掌大,一边有一寸长一筷子宽顺弧的带浅槽的铁把,棉线绳儿做的灯捻子,有时也会用中药“灯草”作灯捻子,捻子大多盘着浸在桐油中,一头搭在灯盏把儿上,汲着桐油,燃着小小的如豆火苗,若有微风吹来,火苗摇曳着飘忽不定,照着昏暗潮湿的屋子。那时全县城都还没电,公家和好点人家点的是煤油灯,我家一盏煤油灯也是放在我那才过门的嫂子房里。就我一人在父亲身边,他似乎少气无力地让我给他拿了一包药喝啦,仿佛是干糙的麻黄色绿豆大小的药丸。这药,后来我总觉得像是一包老鼠药,是否父亲熬不过病痛的折磨,乘家里没人时,让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拿了毒药?是否喝了那老鼠药就死啦?我那时太小,全然不知。可几十年抹不掉这影子阴影,几十年也从没一个大人提起过,也许没这事儿吧。但我抹不去这一丝记忆的影子,愈发觉得,父亲的死是为了解脱我们,这是永远的迷。
要说“三岁看到老”,弱苗的我,这一辈子可能“出息”也不大。
(待续:三、发蒙儿)